缘因
 点击:279 发表:2026-01-20 09:28:54
点击:279 发表:2026-01-20 09:28: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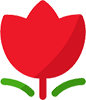 1
1

姚敦义再次离家时,村里人都不意外。且不说他近十年都在外从军征战,吃过喝过见识过,据说还有过女人和孩子,就说他的精神头,他的身子骨,他的一双大手和大脚,平时说的做的,明显不是寻常人。
“敦义是做大事的。”
“敦义是奔着前程呢!他要不走,也跟你我一样守着这山这坡这黄土,谁还瞧得起他?”
“哪怕像他阿耶一样战死,敦义也一定得走。这一点我早看出来了。一年前他回来那天我就跟家妇说过,我说敦义不管在家待多久,一准还得走。他不走就不是他阿耶的崽。”
村里人对此达成共识,除了雪雁。她觉得姚敦义不该走。
十年前,姚敦义随他阿耶姚三木第一次离家时,跟的是苻家军,那年他刚满十六岁。姚家女人流着眼泪从四邻借来两升麦粉,要给爷俩蒸饼子带上,被男人连声呵斥:
“谁要你出去借?”
“可是家里只有半袋粟米。”
“我们要去军营,什么吃不着?”说完,姚三木大笑出门。姚敦义跟在后面。
当时雪雁六岁。
雪雁长得小,六岁时是寻常孩子三岁模样。这要怪她阿娘生得瘦小。她阿娘是南地汉人,随自己耶娘逃荒时走散,被军队顺走做了杂役。在一次战事中,羌人胜利,雪雁阿娘随几百汉人一起被俘。当时雪雁阿耶在军中当伙夫,看来了一群俘虏,就跟头目要人帮忙干活,分得身材瘦小的雪雁阿娘。
雪雁阿耶在羌人里身材高大,高耸的颧骨像经年因打斗而磨秃的牛角。他从未有过女人,也没动过任何心思。战事频繁,他一天到晚埋锅造饭忙不迭。说来奇怪,如今他硬是觉得雪雁阿娘生得有趣,二话不说,就在忙碌间隙把雪雁阿娘推倒在地,生生把自己的家伙插进雪燕阿娘热乎乎的身子里。
雪雁阿娘刚刚成年,哪里抗得住,疼得龇牙咧嘴一直喊叫挣扎,结果反倒刺激了男人。再以后他但凡有空就要弄,直到她怀上雪雁。
两场战事之间,雪雁阿耶把母女俩送回老家,大山深处的一片丘陵地。如果不是大队人马推进到此,或土生土长的山里人,外人轻易不会发现这个地方。雪雁阿耶多次设想自家耶娘看见儿子一家三口的高兴情景,没想到人去房空。几年前老两口一个病死,一个饿死,邻居帮忙埋到后山。
雪雁阿耶留下母女俩,说自己两三年内准回来,说眼见着战事一边倒,自己这头赢定了,到时会带着钱粮回来。但此后再无音讯。
村里人说,男人要么不出去,只要出去,基本都回不来,要么战死,要么各种死,总之回不来。
雪雁阿娘仗着是南地汉人,天生会种地,一个小身量的女人家不仅把公婆留下的地打理得好,自己还在山边角落垦出两亩薄田,够娘俩吃的。村里汉氐羌杂胡都是服气的。
早年姚敦义离家时,雪雁与村里几个娃娃一起跟在后面跑着看热闹,听到了姚敦义阿耶的大笑和他阿娘的哭泣。姚敦义看也没看雪雁一眼。小小一只女娃,流着两筒鼻涕,没什么好看的。
姚敦义再回来,雪雁十六岁,长得十二三的模样,靠在姚家门口,一双圆圆的眼睛牢牢盯住姚敦义。他比村里所有男人都高大,鼻子比所有人都直,眼睛像山上的老鹰,许能看见十里外的猎物。
姚敦义的眼睛扫到雪雁时,停顿片刻。一个小女娃,两只圆眼分得很开,间隔比一般汉人都宽,脸也是汉人那种宽脸。
看见姚敦义瞅自己,雪雁在门口蹲下身,随手拿起一根枝条划拉尘土,也不具体划拉什么,眼睛一直落在姚敦义身上。
姚敦义阿娘听说男人早几年死在战场,扯声哭了两天,眼睛都肿了,但好歹儿子回来了,还带回一口袋钱币,长这么老大,从没见过这么多宝贝,心里稍感安慰。娘俩连夜把钱币埋灶台旁地下二尺。如果再无战事,这辈子许安逸了。
姚敦义阿娘心情日渐转好,本来将死的身体硬朗起来。更开心的是,从儿子回来那天起,雪雁姑娘就隔三差五来家里帮忙干活。跟着她来的,是家里的热闹,这可是十来年没有过的情景。
“姚阿娘!我阿娘晒的干菜,我给你拿来些,你给敦义阿哥做着吃。”说完,雪雁放下干菜,扭身蹲到灶下捅火。每次来,雪雁都借口送东西,然后帮忙干活,嘴里说东说西,逗老太太开心。
雪雁阿娘发现后不让雪雁再拿东西,说自家所剩不多,还要过冬呢。雪雁就空手来姚家,偎在姚阿娘身边说话,不错眼珠地看着姚敦义。
“你总过来帮我阿娘干活,你阿娘肯吗?”姚敦义觉得雪雁心眼不很够用。
“我阿娘不管我。我阿娘就我一个崽。她要管我,我就不回去了。我阿娘什么都能想明白。”
姚敦义觉得女娃好笑,就笑了笑。又过几天,他发现雪雁喜欢说话,有人时对话,没人时自说自话,说得热热闹闹,好像旁边许多人在听。阿娘喜欢就好,姚敦义对此只是笑笑,不说什么 。
明白人看出门道,过来对姚老太太说,雪雁八成看上你儿,抓紧给两个年轻人成亲吧。
姚老太太说汉人讲究,可能需要提亲。
雪雁阿娘听闻此事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她知道雪雁看上姚敦义,兵荒马乱的年头,有个男人守着,多少安稳些。
但也未必,当初,自己就是随耶娘一起逃难,两个人守一个娃,还是走散了。到底都是命。再说,姚敦义模样身板都太好,雪雁能擎受住吗?更主要的是,他在外面荒跑十年,心怕是野了,怎么甘心守家在地,过农人日子?
提亲的上门了,是周家女人,能说会道,男人在村里也拿事。
“我看敦义够懂事,一回家就帮他阿娘干活,快把一年的烧柴砍回来了。你俩家的地离得也不远,两个娃成亲后,一起养你们老俩,多好!”
“话是这么说,可我们是汉人。姚家可愿意?”
“姚老太太得意你家雪雁,说她一来家里就热闹,还能干活。现在不论汉人不汉人的。我也是汉人,嫁的可是氐人呢。兵荒马乱的,不论这些。早成家早安身不是。”
“话是这么说,我得问雪雁愿意不。”
“还愿意不?你家雪雁天天往姚家跑,天天围着姚家娘俩儿转悠,我看都快上榻了。”
雪雁阿娘扬手轻轻打了周家女人一下,嗔怪地骂了一句家乡话。周家女人没听清楚,但知道自己说着了,临走时撂下一句话:“你要是同意,我让姚老太太送一只羊过来,算是定礼。”
村里人都看出来了,姚敦义这次回来,肯定带回不少钱币,不然不会一下子从山下大镇买回三只羊,那可不是寻常人家养得起的。
雪雁阿娘没说话。她希望雪雁今天早些回来,娘俩儿把话说清楚。村里没有几户汉人,娘俩夹杂其间,没有男人依靠,好歹过了十几年,没出过大事,她知足。她吃过苦头,从当年与耶娘离别,到落在异族手里,到被雪雁阿耶日夜强暴,她都挺过来了。只是,从前的波折经历让她始终心存不安,不知还会发生什么。她不太管雪雁,不能说与痛恨她阿耶当年的暴行无关,虽每每细看雪雁眉目脸庞,实实在在汉人模样。唉!好歹喂吃喂喝养大就是。她由着雪雁跟其他小孩子嬉戏玩耍,爬山上树随其意,一切命定,她不争执。天下不太平,能活一天算一天,没人知道第二天早晨醒来会发生什么,醒不醒来都难说。
当天晚上,雪雁阿娘没等回雪雁。
当天白天,姚敦义去山上放羊,雪雁跟了去,歇息时贴着姚敦义坐在土岗上,跟姚敦义说东说西,又问姚敦义战场上的事儿。后来两人抱到一处。太阳落山时两人赶羊下山,雪雁没回家。姚敦义赶她走,她拗着不走。姚老太太说吃过饭再走吧,我蒸了麦饼。
吃完饭天全黑了。雪雁说自己不敢回家。姚敦义憋住笑,说我送你,抹了嘴巴起身送雪雁。半路上,雪雁突然把袍子撩开,说你摸摸我再回去,我想让你一直摸我。
姚敦义把雪雁抱起来扛到肩上,扛回自己家,扔到自己榻上。姚老太太耳朵不很好使,但吱吱嘎嘎的榻板挤压声还是听到后半夜。
第二天,姚老太太让姚敦义牵一只羊送雪雁阿娘。雪雁阿娘看了看姚敦义,看到了姚敦义的平静无常,想说什么,又觉多说无用,就把羊接过来,拴到木栅栏上,自己回头进屋。
姚敦义回到家。姚老太太问雪雁阿娘说了什么。
“什么也没说,自己回屋了。”
“没让你进屋问话?”
“没让。”
娘俩说话时,雪雁最初靠在门口听了几句,转身出门抱了一捆柴禾扔到灶下,兀自做饭。
“没人信我。我早知道阿娘不会拦我。阿娘疼我,知道我要什么。五岁时我想爬树,阿娘就让我爬,知道我不会摔下来。七岁时我在山下大镇跟一头羊顶头,阿娘知道我能,知道我不会输,也不管我。现在我看上了男人,村里最好的男人,哪里都好,身材最高,鼻子也最高,笑起来全村最好看。阿娘不会不同意。我想做什么,阿娘从来不反对。阿娘知道她崽能……”
姚家母子断断续续听着雪雁的自言自语,相视而笑。
半月后,姚敦义去大镇买盐,回来时牵了一匹马,对阿娘说他转天要离家从军。
“将军领兵驻扎大镇。镇里镇外全是人,总有几万。”
“还要打仗?”
“先往西走,打不打仗听将军的。听他的准没错。从前有个弟兄现在跟在将军身边,喊我一起去。准没错。”
“雪雁怎么办?”姚老太太冲窗外努嘴。
姚敦义回来时,雪雁正喂羊,眼下站在窗口听屋里说话。
“随她。想在姚家,留下;想回自己家,由她。反正也没迎娶。”
“怕是不成。她们汉人计较。”
“再计较还能怎样?将军到大镇了,我不能不跟着。这辈子可能就这一个机会追随将军了。”
晚间,雪雁跟姚敦义睡在一起。姚敦义没提转天要走的事。他知道雪雁有些痴,说了怕误事。他计划天不亮就走。
雪雁这晚十分起劲儿,在姚敦义身上手脚不停上下翻飞,百般侍弄,小小身量如母鸡跳上牛背,搞得姚敦义精疲力竭。在沉沉睡去之前,他想起阿耶死前曾为他抢来的羌人女子,个头是不小,眉眼也不丑,实没有雪雁会耍。他通体畅快,一度不舍,想带上这个汉人女娃一起走。
姚敦义鼾声大作时,雪雁起来了。她蹑手蹑脚走到姚老太太榻前,听到了熟悉的呼噜声。确定娘俩都睡实后,雪雁轻轻推开房门,走进月亮地,从石磨上拿起马嚼子给马戴上,牵马去了后山,把马拴到树林里一棵黄连枝干上,自己则转回身,在村旁高岗寻了一个隐蔽处,静静坐下,等待天亮。
晨色朦胧。
雪雁看见姚敦义走出家门。姚阿娘跟着身后。姚敦义停了片刻,跟阿娘说着什么,比比划划。两人一同去了雪雁家,很快又出来。再后来,姚敦义一个人朝大镇的方向走去。
雪雁瞬间窜起,飞奔过去,如荒野疾风,又如狡兔速逃。这是她从小在林间自己取乐的游戏,穿林跃树,腾挪自如。转眼间,她就在坡顶立在了姚敦义面前。
下了这道坡,就离大镇不远了。
姚敦义神情难看,问她把马牵哪里了。
“你让我怀上孩子再走。”雪雁仰头望天。
“我问你把马牵哪里了?”
“让我怀上孩子,我不拦你。有了你的孩子,我就能像我阿娘一样一个人过下去。”说着,雪雁上前抱住姚敦义。她身量小,头顶勉强够着姚敦义胸口。姚敦义一把推倒她,自顾往大镇方向走。雪雁扑过去抱住姚敦义一条腿,被姚敦义一脚踹到胸口,滚下坡去。
姚敦义再次离家,村里人都不觉意外。且不说他十年里都在外从军征战,吃过喝过见识过,据说还有过女人和孩子,就说他的精神头,他的身子骨,他的一双大手和大脚,平时说的做的,明显不是寻常人。
“敦义是做大事的。”
“敦义是奔着出息走呢。他要不走,也跟你我一样守着这山这坡这黄土,谁还瞧得起他?”
“哪怕像他阿耶一样战死,敦义也一定得走,这一点我早看出来了。一年前他回来那天我就跟家妇说过,我说敦义不管在家待多久,一准还是要走。他不走就不是他阿耶的崽。”
村里人对此达成共识。
八年后,姚敦义第二次回到故乡,手拄竹杖,跛着一条腿。他先到大镇停了停,两天后才回家。
他跛得厉害,半身倾斜,每走一步都要用力。从大镇走了小半个上午,歇了几次,他才上得山坡,看见老家模样。还是那几十间草舍。他长长松口气,脸上的表情松弛下来。
一个少年跟在身后。少年阿耶死在战场,临终前托孤。姚敦义负伤卸甲后,去函谷关旁的村里接来少年,一起回家。他要接阿娘到大镇住。镇里人几乎被连年征战灭绝,房屋大都空着。他已选好一间,收拾出来。这样的腿脚,不能再种地打柴了。
姚敦义在自家木栅前站了一会儿。房子破旧,草顶石头墙,早年阿祖盖的。那之前阿祖不住中土,住河西。河西没人住石墙草房,住的是帐篷。
“阿娘!”姚敦义高喊一声。
房门推开,一个女子立在门口,矮矮的身子。姚敦义端详半天才认出是雪雁。她右脸一道斜疤,左眼凸着一个紫黑色肉球,甚是吓人。
“姚阿娘死了。”
“多会死的?”
“五年前。”
“怎么死的?”
“病死的。她胸口疼。”
“埋哪了?”
“后山。”
雪雁没说是自己埋的,没说姚阿娘病了半年多,都是自己照管吃喝。她是躺在自己怀里咽气的。姚敦义进屋,坐在阿娘榻上流了一会眼泪,然后拄着竹拐,扶着少年,随雪雁去后山祭拜。他跪在坟前,流着眼泪说了说自己这些年的情况,跟着将军出征,连升三级,官至都尉,吃喝用度不愁,还被将军赏过女人,可惜女人命薄,病死了,等等。
雪雁蹲在不远处,拿着一根枯树枝低头划拉地上的尘土,姚敦义的话一字不落地听进耳朵。
晚间,雪雁做了粟米粥。姚敦义问了她家的情况。雪雁说自己阿娘也死了,上山砍柴时滚到坡下,头撞到石头上。
“我阿娘的坟挨着姚阿娘的坟。夜里她俩能说说话。”
夜里,姚敦义睡阿娘的榻,雪雁睡姚敦义的榻,少年睡灶下。天气渐冷,姚敦义的伤腿隐隐作痛,躺在榻上翻来覆去,午夜才入眠,总算睡了一个时辰。再醒时,他听到雪雁和少年都在打呼噜。
姚敦义翻身起来。他担心雪雁,怕她像从前一样纠缠自己。那张脸比鬼吓人,谁敢要她?但,毕竟她替自己照顾了阿娘,不好与她撕破脸。想着,他悄悄叫醒少年,推门而去,前往大镇。
姚敦义整条腿使不上劲,好半天也走不多远。眼见着天亮了。
突然,姚敦义停住脚步。他忘了拿走埋在灶下的钱币。
许是雪雁脸上的疤痕太过恐怖与刺激,让他乱了阵脚。
姚敦义费了好大力气,重新走回自家院落。站在房门口。屋里有人说话,是雪雁的声音:
“大镇的人都死光了。没死的都要死。周围都是死人,一刮风就有臭味过来,活人待不了。谁去谁死。姚阿娘死了。我阿娘也死了。你早晚也要死。你走吧。你十有八九会死在大镇,我说话有准头。
“我不会死。我阿娘说我命大。我被你一脚从坡上踹下来,只捅瞎一只眼。枯树枝插进眼窝了。另一只眼睛好好的,什么都能看见,不耽误干活。脸被石头割烂了,我抓了一把土涂上,那么深的口子塞满了土,当时血就住了。我阿娘说山上的黄土药性好,能治病。
“你有两只眼睛也是没用的。阿娘死后我离家寻你,一路寻到将军帐下,在马厩干活。干了一年多。你从我眼前走过好几次都没认出我来。你有两只眼也是没用的。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比谁都不差。你跟女人在榻上弄我都看见了。她除了奶子比我大,根本没有我伺候你的本事。头人赏你你用就是。后来那个女人是你打仗抢来的,你还把人家的孩子抢来扔坡下了。那个坡跟我摔下去的坡差不多,遇到枯树枝也会把眼扎瞎,遇到石头也会把脸割烂,遇到野狗直接就被掏了。我那天也遇到野狗了,但我会上树。我在树上藏到第二天天光大亮才回家。后来我去后山牵回你的马,拿牠练功,上马下马如走平地,信不信我能追上兔子?我练成了。姚阿娘和我阿娘都死了,我才去找你。我不恨你,但你不该跟女人睡觉时把我的事讲给她听。你一边说还一边大笑。你笑吧!我把我阿娘砍柴的砍刀磨得比风都快。你在战场上砍人时,我拿我阿娘的砍柴刀在你眼皮底下砍了你的腿,趁你不注意又剁了第二刀。呵呵!你以后什么也干不成……随便你去哪里!你去哪里也是个废人……”
【编者按】这篇文字以乱世为底色,铺展了一场裹挟着欲望、背叛与复仇的命运纠葛。雪雁与姚敦义的羁绊,从少女炽热的执念到最终惨烈的反噬,道尽了动荡年代个体的身不由己。乱世消解了温情与道义,雪雁阿娘的遭遇、雪雁的被弃与复仇,都揭示着动荡对人性的扭曲。缘起缘又落,所谓 "前程" 与 "安稳",在乱世里不过是相互伤害的幌子,留下的只有破碎的人生与无法弥合的伤痕。推荐阅读。编辑:梁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