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日子过进文字里,再把文字写回日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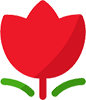 1
1
 俺的书桌,就摆在老槐树的窗下。晨光淌过窗棂,在砚台上洇开一圈淡金的光晕,砚沿还沾着昨夜未干的墨渍,像日子漫过岁月的浅痕。案头的稿纸叠了半尺高,最上面那张摊着,写着“槐香”二字,笔尖划过的纹路深浅不一——这不是什么宏大的题材,只是清晨推开窗时,风里裹着的那缕清甜,落进纸页间,就成了文字的根。
俺的书桌,就摆在老槐树的窗下。晨光淌过窗棂,在砚台上洇开一圈淡金的光晕,砚沿还沾着昨夜未干的墨渍,像日子漫过岁月的浅痕。案头的稿纸叠了半尺高,最上面那张摊着,写着“槐香”二字,笔尖划过的纹路深浅不一——这不是什么宏大的题材,只是清晨推开窗时,风里裹着的那缕清甜,落进纸页间,就成了文字的根。
总有人问俺,文字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俺笑一笑,抬手指了指窗台上的那筐槐花。这是今早刚捋的,老伴正坐在院里择,白花花的花瓣簌簌落了一地,像撒了一场碎雪。俺说,你看这槐花,蒸了是饭,晒了是茶,落在纸上,就是诗。这话,是俺娘教给俺的。
那年月,日子苦得像嚼碎的黄连,俺娘目不识丁,却攥着一把旧剪刀,把苦日子裁成了红纸上的纹样。她剪的喜鹊登梅,翅尖上沾着灶间的烟火;剪的五谷丰登,穗尖里藏着田间的风霜。那些红纸,是俺们兄妹几个的启蒙课本,也是娘没说出口的千言万语,藏着她对日子的热望。俺就是在那时懂得,日子这东西,你把它过细了,它就成了文字;你把文字写暖了,它就又成了日子。
年轻的时候,俺扛着锄头在田里刨食,汗珠砸进泥土里,溅起细小的尘星。那时总觉得,日子是粗糙的,是锄头啃过的土坷垃,是镰刀割过的麦秸秆,是灶台上总也蒸不软的窝头。后来去了部队,嘹亮的军号声里,俺开始学着把这些日子记下来。写训练场上滚热的汗水,写战友们深夜均匀的鼾声,写月光下站岗时,风里捎来的家乡槐花香。
那些文字没有华丽辞藻,却像军用水壶里的凉白开,解渴,更暖心。就像路遥笔下的黄土地,每一粒泥土里都藏着庄稼人的坚韧;每一行文字里都埋着俺对生活的赤诚。那时俺才明白,铁凝说的“文学要贴着地面飞行”,原来是这个道理——文字不是悬在半空的云,是踩在脚下的路,是地里长出的苗,是日子里熬出的暖。
再后来,俺回到了家乡,守着这间小书房,守着窗外那棵老槐树。日子慢了下来,像老屋里的那口钟,滴答滴答,敲着岁月的节拍。俺开始写更多细碎的日子:母亲的剪纸、父亲的烟袋、老槐树下的棋摊、村口的煎饼鏊子。俺写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却都是俺实实在在过过的光阴。
琼瑶笔下的深情,于俺而言不是风花雪月的缠绵,是母亲缝在衣缝里的牵挂;林徽因笔下的诗意,也不是亭台楼阁的雅致,是晨光淌过窗棂时,落在砚台上的那圈金晕。俺的文字,就像俺们鲁南的煎饼,粗糙却有嚼头,朴素却藏着麦香。
昨夜,俺又在昏黄的灯下写字,写着写着,就想起了年轻时的事。那时俺在部队,给家里写信,总只写些“一切都好,勿念”的话。娘不识字,却总把俺的信揣在贴身的衣兜里,逢人就笑着说:“俺儿又来信了。”后来俺才懂,那些信里没说透的牵挂,娘都懂。
墨汁不小心溅在稿纸上,晕开一小朵墨云。俺忽然懂了,文字这东西,本就是一条河——日子是源头的活水,从笔尖流出来,又淌回日子里,兜兜转转,便成了岁月的长河。
如今,俺的鬓角早已染白,案头的稿纸却依旧堆叠得高高的,笔下的文字也依旧滚烫。俺总跟人说,俺不是啥作家,只是个把日子过成文字的庄稼人。俺把锄头啃过的泥土写进文字,文字便有了筋骨;把母亲剪过的红纸写进文字,文字便有了温度;把老槐树的清香写进文字,文字便有了灵魂。
窗外的风又起了,槐香漫过书桌,轻轻落在稿纸上。俺拿起笔,在空白处又写下一行字:把日子过进文字里,再把文字写回日子里。这不是啥创作秘诀,只是一个庄稼人对生活最朴素的告白。就像院外的老槐树,年年岁岁枝繁叶茂,把根扎进厚实的泥土里,把花开在流转的岁月里,把那些没说完的故事,悄悄藏在风里。
【编者按】本文以质朴温厚的笔触,勾连起耕读岁月中文字与生活的双向流淌。一方砚台、几页稿纸、窗外槐香,皆成为时间的信物,见证着作者如何将粗粝的日子沉淀为有筋骨、有温度的文字,又让这些文字反过来滋养平凡光阴。这不仅是文学的实践,更是一种生命哲学——在泥土与笔墨之间,完成对生活最诚恳的叙事。推荐阅读。编辑:冬青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