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盘上的月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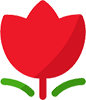 1
1

一到冬天,我和姐姐踩着冻得硬邦邦的街巷,来到村前的石碾旁。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白天,姐姐跟着队里上坡挣工分。天刚蒙蒙亮,她就背着篓子,扛着铁锨出门。那阵子正是冬修水利的季节,村里的劳力都集中到坡里挖沟整地。中午收工回来,她会背回一些柴草,裤腿上溅满了泥点,鞋帮上也沾满了泥巴,额头上却冒着汗。娘给她舀了一碗地瓜粥,她端起碗,呼噜呼噜几口就喝完了,又抓起几个地瓜,狼吞虎咽往嘴里塞,像是要把一整天的力气都补回来。吃完,她只在炕沿上歪了一会儿,就又被队里的钟声催着上了坡。
傍晚收工时,她的手掌被铁锨磨出了水泡,钻心地疼。娘心疼的掉泪,她却总是笑笑,说:“没事,过两天就好了。”等煤油灯点上,她又坐到灯下,补那些被树枝挂破的旧衣服,手里的针线在布面上穿梭,像白天在坡里干活一样认真。
那几年,村里的几个跟姐姐同龄的闺女,一个个都远嫁外地。有的去了外地县城的村庄,有的干脆嫁到更远的煤矿附近,说是那边日子好过些,有白面吃,有细布穿。媒人也来过家里几回,说有个外县的小伙子,家里有几间砖房,还在公社里有个临时工的差事,只要姐姐愿意,就能过去享福。娘心里动过,悄悄抹过几回泪,说:“你要是走了,好歹能穿上件像样的棉袄。”
姐姐却只是低头纳鞋底,半晌才抬起头,说:“娘,我不走。天寒饿不死家家雀儿,我就不信人一辈子能穷到底。”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像是看着煤油灯,又像是看着更远的什么地方。
夜已经深了,村子被一层薄薄的霜气罩着,屋顶的茅草在月光下泛着灰白,像披了件旧蓑衣。远处的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天空,被月光勾勒出清晰的轮廓,像一幅没画完的炭笔画。空气冷得发干,吸进肺里,带着一股土腥和柴火烟的味道,又凉又辣。
我们按照母亲的吩咐,要把半口袋地瓜干碾碎、碾细。明天早上,母亲要给我们做“地瓜豆”喝——其实就是一碗地瓜干糊糊。那时候,口粮还按工分和人头分,细粮少,粗粮多,地瓜干是一年四季的主食。谁家要是能顿顿喝上地瓜豆,就算是过得去的人家了。
月亮慢慢爬上来。后来越升越高,光也越来越亮,终于照亮了石碾屋,照亮了碾盘。说是屋,其实就是一圈人头高的土墙,中间空着,只在靠墙的一边放了些苞米秸秆,也好挡风。墙留了个豁口,方便人进出。墙外是一条被人踩得发亮的土路,路边稀稀拉拉长着几丛枯黄的草,草叶上结着细霜,被月光照得晶晶亮。石碾紧靠着队里的牲口屋和仓库,再往前,生产队的打麦场静静卧着,麦秸垛和苞米秸秆垛,仿佛一个个沉默的巨人,在月光下守着空荡荡的场院。
我和姐姐一推一拉。姐姐推着磨棍,身子微微前倾,像在跟石碾较劲;我在前头拉着,脚跟在冻地上打滑,脚冷,冷得我把脚尖往地上抠。我跺跺脚,跺得地面“咚咚”响,嘴唇哆哆嗦嗦着说冷。姐姐喘着气,却还是硬着嗓子催我:“快拉,快拉就不冷了。”
石碾吱呦吱呦地响着,仿佛在吟唱一首古老的歌谣。那声音不响亮,却拖得很长,仿佛是从很远的年代里传过来,绕着磨盘转,又绕着我们的影子转。它一响,夜就显得更静;它一停,望得见不远处村口那个大湾。湾里结了冰,在月光下朦朦胧胧。
姐姐在后头还要不时地扫着碾出的碎地瓜干。她拿着一把小扫帚,扫帚毛被磨得稀稀拉拉,却还能用。她弯下腰,把磨盘边上的碎渣扫到中间。她的手冻得通红,指节粗粗的,手背裂开了几道口子,可她顾不上疼,只顾着把活干得仔细些——母亲吩咐过,地瓜干不能碾得太粗。
月光落在磨盘上,像一层薄薄的霜。磨盘是白色的石头,被岁月磨得发亮。地瓜干在碾磙下一点点碎开,有的变成细粉,有的还是小粒,散在磨盘上,被月光照得发白。我一边拉着磨棍,一边偷偷盯着那一圈圈旋转的影子:碾磙的影子、磨棍的影子、姐姐的影子、我的影子,都在月光里转,转得人眼发花。我忽然觉得,那石碾像是要把这清冷的冬夜也一点点碾碎了,融进这细碎的地瓜面里。
风从豁口灌进来,卷起地上的细土和糠皮,扑在脸上,迷得人睁不开眼。土墙挡不住多少寒气,只把风的声音挡得有些发闷,像有人在墙外头叹气。墙外的几棵老槐树,枝条被风刮得轻轻摇晃,影子在地上来回摆动,像在给石碾打着拍子。远处村里的狗偶尔叫两声,很快又安静下来,只剩下石碾单调的吱呦声,在月光里一圈圈荡开去。
我穿着母亲做的旧棉袄,袖口磨得发亮,露出里面发黄的棉絮。那是母亲亲手织的布,母亲精打细算,一件棉袄要穿好几个冬天,。风从袖口往里钻,我忍不住又跺了跺脚。姐姐回头瞪了我一眼,说:“别偷懒,碾不完,娘明天拿啥给你做地瓜豆?”她嘴上这么说,手底下却把绳子往外拽了拽,让我少用点力。我心里明白,却装作不知道,只是把冻得发红的手往袖子里缩了缩,继续往前拉。
磨盘上的地瓜干渐渐少了,碾出的面却越积越多。姐姐停下来,用扫帚把磨盘边上的碎渣一点点扫到中间,又伸手抓了一把,放在手心里捻了捻,对着月光看了看,说:“还得再碾一遍,不能太粗了。”
我有些不耐烦,嘟囔着:“差不多就行了,这么冷的天,谁还管细不细。”姐姐没理我,只是把那半口袋地瓜干又倒了一些在磨盘上。石碾重新转动起来,吱呦声又在夜色里响起来,像是被谁拉长了的叹息。
月亮越升越高,把石碾屋的影子拉得很长,土墙的轮廓在月光里显得有些模糊,像是随时会被风刮走。墙外的土路向远处延伸,被月光照得发白,像一条静静的小河。路边的土块、碎石、枯草,都被镀上了一层淡淡的光,显得柔和了许多。我抬头看了一眼月亮,觉得它离我很远,又觉得它就挂在头顶上,跟着我们、跟着石碾一起转。磨盘转一圈,月光也跟着转一圈,把我们的影子一会儿拉长,一会儿缩短。我忽然有点恍惚,仿佛这石碾、这月光、这冬夜,都在一个梦里,而我和姐姐,就困在这一圈圈的旋转里,走不出去。
姐姐大概是看出了我的走神,说:“困了?困了就回去睡。”我赶紧摇头,说不困。其实我是怕回去挨骂,也怕明早真的喝不上那碗热乎乎的地瓜豆。那点糊香味,在这冷得发疼的冬夜里,是实实在在的盼头。母亲常说:“有口吃的,就不算苦。”她说话的时候,总爱看着我们,像是在安慰我们,也像是在安慰她自己。那时候,我不懂她话里的意思,只知道地瓜干糊糊喝多了烧心,嘴里发酸,可真要是闻不到那股糊香味,心里又空落落的。
石碾又转了不知多少圈,我的手渐渐没那么冷了,额头反而冒出了一点汗。棉袄里有些热气,和外面的寒气一撞,我打了个喷嚏。姐姐停下脚步,说:“歇会儿吧。”
墙外的风从豁口吹进来,把地上的糠皮吹得打旋,在空中转了几圈,又落回磨盘上。我和姐姐靠着磨盘站着。姐姐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皱巴巴的手帕,一层层打开,里面包着半块干硬的玉米面饼子。那是母亲下午留给她的,她一直没舍得吃。
“给你吃。”她把饼子掰了一半递给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来,咬了一口,牙都被硌得生疼。饼子又干又硬,我一点点嚼着,却觉得满嘴都是香味。姐姐看着我笑了笑,说:“慢点吃,别噎着。”她自己也咬了一口,嚼得很用力,腮帮子鼓起来。
月光落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被冻得发红,嘴角却带着一点笑意。远处村里偶尔传来几声咳嗽,还有谁家孩子的哭声,很快又被大人哄住。那哭声在夜里显得格外脆,像一根细针,轻轻扎一下,又很快消失。村子里的灯光稀稀落落,从窗纸后面透出来,虽然温暖但十分暗淡。
歇了一会儿,姐姐忽然抬头看着月亮,说:“你说,将来要是有机器磨面,该多好。”
我愣了一下,顺着她的目光看向月亮,又回头看了看那沉重的石碾,说:“啥机器磨面?”
姐姐眯起眼睛,像是在想象,又像是在给我讲一个遥远的故事:“就是那种——不用人推,也不用人拉,只要把地瓜干倒进去,机器嗡嗡响,出来就是细细的面。咱就不用半夜里出来挨冻了,在家等着装面就行了。”
我听得入神,嘴里的饼子都忘了嚼:“那机器得多厉害呀?”
“肯定厉害。”姐姐笑了笑,指了指磨盘,“到那时候,石碾就不用了,就在这儿晒太阳。咱们也不用在这儿转圈圈了。”
我赶紧接话:“那我要让机器给我磨好多好多面,天天吃白面馒头,再也不用吃地瓜喝地瓜豆了。”
姐姐轻轻敲了敲我的头:“你呀,就知道吃。不过,你说得对,我也想吃白面馒头。”
月光静静洒在我们身上,也洒在那一圈圈磨痕上。那一刻,我仿佛真的看见了一台大机器,在月光下转动,发出嗡嗡的声音,把我们的影子都震得轻轻晃动。我忍不住伸出手,在空中比画了一下,像是在摸着那台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大机器。
歇了一小会儿,姐姐拍了拍手,说:“行了,再碾最后一圈,碾完就回去。”我身上的汗消了,觉得有着冷了,便拉紧了绳子。石碾再次转动起来,吱呦声比刚才轻了一些,仿佛也累了。可它还是一圈一圈地转,把地瓜干碾得更细,把月光碾得更碎,把我们的影子碾得更长。
磨盘上的地瓜面终于变得细了,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光,像一层薄薄的雪。姐姐把地瓜面拢在一起,一瓢瓢进口袋里。我在一旁帮她扶着袋口,看着那袋地瓜面一点点鼓起来,心里突然踏实了许多——明天早上,娘的锅里,又有东西可以翻滚了。
月亮偏西了一些,石碾屋的影子换了个方向。风小了些,却更冷了,冷得人骨头缝里都发麻。远处村口的那片杨树林,在月光下只剩下一片深黑的轮廓,树枝交错,像一张巨大的网,把半个天空都罩住了。姐姐把布袋扛在肩上,布袋不重,却压得她肩膀发沉。我们踩着月光往回走。街巷还是那样硬邦邦的,脚下的土冻得像石头,每走一步,都发出轻微的声响,在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路过大湾时,湾里早结了冰,月光照在冰面上,亮得刺眼。若是白天,我便在冰面上滑冰,去看被冻住了的芦苇,夜里却是不敢的,生怕摔了大跟头,跌个鼻青眼肿。我下意识地往旁边躲了躲,姐姐喊我说:“离湾沿远点,别滑下去。”她的声音很有力,像一根绳子,把我从那片黑里拽回来。
回到家门口,母亲还没睡,灶房里透出一点昏黄的光。门“吱呀”一声开了,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带着柴火的味道。院子里的鸡窝静悄悄的,几只鸡把头埋在翅膀底下,缩成一团。院子角落的柴垛被月光照得发白,像一座小小的山。母亲从灶前抬起头,看了看我们,又看了看布袋,说:“碾好了?快进来,外头冷。”她的声音不大,却像火一样,一下子把我们身上的寒气烤化了些。
很多年以后,我再想起那个冬夜,记忆里最清晰的,不是冻得发疼的手脚,也不是那碗热乎乎的地瓜豆,而是磨盘上的月光,和姐姐那句“将来要是有机器磨面,该多好”。那月光安静、清冷,却又带着一点说不出的温柔,像是母亲在灶前忙碌的身影,像是姐姐递过来的半块干饼子,也像是那些被石碾碾碎的日子——苦,却磨出了细细的光。
后来,土地承包到户,村里人心浮动,有人抢着包好地,有人怕担风险,只包了口粮田。姐姐却咬咬牙,把离家远、土质差的几亩坡地也一并承包了下来。村里人背地里说她“傻”,说她“逞能”,娘也替她捏了一把汗,说:“你一个闺女家,折腾这些干啥?”姐姐只是笑笑,说:“天寒饿不死家家雀儿,我就不信人一辈子能穷到底。”
那几年,她像上了发条一样,白天在地里忙,晚上在灯下算账、看书,学人家怎么施肥、怎么选种。春天,她一个人牵着牛在坡地上犁地,牛蹄踩在湿泥里,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夏天,她顶着毒日头在地里锄草,背上的汗把衣服浸得透湿;秋天,她站在高高的麦垛上,把一捆捆麦子往车上扔,胳膊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
慢慢地,坡地里长出了像样的庄稼,地里的收成一年比一年好。她和姐夫又买了拖拉机,帮村里人耕地、拉庄稼,小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年回家时,她穿着得体的羽绒服,给娘买了新衣裳,给我塞红包,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如今,村里的石碾早已不见了,磨盘也不知被谁搬去垫了墙角。土路被水泥抹平,路边的荒草被整齐的树取代,夜晚的村庄被路灯照得通亮,再也看不见那样清冽的月光。偶尔,我还会下意识地朝村前望一眼,仿佛还能看到那一圈圈旋转的影子,听到那熟悉的吱呦声,在月光里慢慢远去。
我知道,有些东西是不会消失的。它们就像那磨盘上的月光,落在记忆的深处,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轻轻照一下,让你在喧嚣的日子里,忽然想起那个寒冷却踏实的冬夜,想起那碗朴素的地瓜豆,想起和你一起推着石碾的人。想起那些被岁月碾过的痕迹,虽然粗糙,却真实;虽然寒冷,却温暖。也会想起姐姐那句话“天寒饿不死家家雀儿,我就不信人一辈子能穷到底”,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像一盏灯,照亮了我们的路。
【编者按】寒夜霜风裹月色,石碾吱呦碾流年。文章堪称一场对岁月温情的“溯源侦破”。作者以“冬夜石碾”为核心物证,月光、冻裂的手、干硬饼子等细节构成关键线索链,层层解锁贫穷年代的生活真相。石碾的吱呦声既是场景标识,更成为串联过往与当下的时间密码,其从“核心生产工具”到“消失垫墙”的变迁,暗合时代发展轨迹。姐姐两次重复的“天寒饿不死家家雀儿”,成为破解人物精神内核的关键证词,串联起冬夜碾磨与日后打拼的行为逻辑。文中冷热触感的交织、味觉嗅觉的留存,构建出立体的“岁月证据场”。这场“侦破”的终极发现,是藏在平凡日常里的亲情力量与生命韧性,让岁月的苦难底色终被温暖晕染。文章在平凡的场景里藏着最真挚的亲情,艰难岁月中育出最蓬勃的生命力。石碾终会老去,月光却永远照亮记忆,让那些粗糙却温暖的过往,成为喧嚣岁月里最安稳的慰藉。推荐阅读赏析!编辑:攀登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