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沧浪河畔”之腊味飘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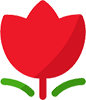 1
1

腊月的风,裹着寒意,却也弥漫着人间烟火里一种悄声无息又温暖至深的独特气息——腊味飘香的味道。
里下河的冬天不算冷,但有一种湿哒哒的寒气,一直往心里钻。越是天冷,越容易让人想起一些热乎的味道。对我来说,冬天真正的开始,是从家里开始准备腊味开始。
腊月的清晨,薄雾氤氲的沧浪河畔,一缕醇厚浓郁的腊肉香气已悄然弥漫。循香而去,还没有高楼林立的商品房的年代,大街小巷各家各户的院子里一根杆子横着,挂满晾晒着一串串红亮油润的香肠,密密麻麻,像喜庆的鞭炮,又似火红的绸缎,微风一吹,轻轻晃动,散发出阵阵香料与鲜肉交织的诱人香气。再瞧屋檐下挂着的咸肉和咸猪头,被阳光照得油光闪闪,像是涂了一层蜜;咸鱼干挺着身子,鳞片闪烁,在晨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孩子们在其下钻来钻去,奔跑打闹,家养的小猫小狗则围着团团转,歪头看着主人,希望得到一口美味。可不是吗!闻着那醉人的腊香,仿佛闻到过年的味道。
这正是晾晒过年“腊味”进行“晒冬”的最佳时节。过年的仪式感,也往往从灌晒香肠开始。寒冬腊月里,随便走进一户人家,都会看到切肉、调料、搅拌、灌香肠、晒香肠的场面。那随处可闻的香喷喷的腊味儿,飘在大街小巷的上空。
在物资不那么丰富的年代,过年可是家里头等大事,准备腌制年货更是重中之重。一进冬月,父母亲就张罗着灌晒香肠。灌香肠绝对是一个技术活,母亲灌得一手好香肠。看天气、选肉质、调口味、晾风晒是母亲灌香肠的四大秘诀。
俗语道“冬腊风腌,蓄以御冬”。年尾十二月被称为“腊月”,这时的天气云量较少且少雨干燥,西北季候风开始流行,肉类不易变质且蚊虫不多,最适合风干制作腊味。入冬后温度在0度以上、10度以下,正是灌香肠的好时候。母亲往往选择晴朗有风的日子,天气干燥,这样香肠容易被风干,一旦错过了这个时节,靠自然条件制作香肠就失去了最佳时机了。
看好了天气,接下来是选好肉质。母亲总是首选一块七分瘦三分肥的猪肉,洗净控干水分后去皮、去骨头以及去肥腻的部分,然后顺着猪肉的纹理,将精选的瘦肉,切成一小条一小条,剁成一小块一小块,母亲从不用绞肉机绞,那样太碎了,影响口感,而是耐心地用刀切,这确实累。其实,更艰巨更累的活儿是刮洗小肠。母亲先把面粉放在小肠上反复揉搓,然后再把小肠翻过来用竹签轻轻的把上面的粘液刮干净,再用盐揉搓,最后用清水反复冲洗,直到小肠变成薄薄的透明状才能使用。
腌制时的配料不用料酒用白酒,再拌上盐、姜、味精、葱、八角、茴香、花椒、桂皮、丁香之类磨成的五香粉。香肠是一个放诸四海皆能接受的美食,加的佐料没有一定比例,所以调料配比就看个人口味喜好而定,把肉块和佐料搅在一起拌匀,腌着。腌制1个小时更入味,腌在佐料里的肉开始散发五香肉的味道,且越来越浓。这时,母亲把洗净的小肠整理好,慢慢套抹在漏斗嘴上开始灌制了。末端用纱线扎紧,母亲一手持稳漏斗,一手把肉块从漏斗灌入肠衣里。这是个细活,稍不留神,动作稍微大一些,猪肠衣就容易被挤破或者肠衣就会从漏斗嘴上滑下去。即便这样,母亲也没有泄气,而是扭扭脖子,转转已经将近麻木的身体,撸起袖子加油干。灌的时候双手连抹带挤,把肉块挤紧实,程度需掌握在不紧不松。灌得太紧,腊肠容易裂;灌得太松,晒出来又皱巴巴的。母亲总说:“灌香肠和做人一样,宽了不行,紧了也不好。”当时不懂,如今回想,那句话倒也挺像冬天里的一句小道理。
香肠灌完了,父亲捏着香肠,母亲开始打结,每隔30公分左右用一根梭子线打结断开,再用热水洗一洗香肠的肠衣表面,系上白线的香肠气鼓鼓的,母亲拿起一根针,到处刺猪肠中的气泡。轻轻一戳,里面的气就迅速溜了出来,而那猪肠就乖乖的贴在肉上了,半成品就算完成了。
父亲拿来一根结实的竹竿,把一节节红通通香喷喷的香肠整齐地绕挂上去,白天放到太阳光下晒,“吃到了”阳光的香肠,油光透亮,晚上收回来,放到干燥通风处,不能受冻。等上大半个月,自家腌制的香肠就算完成了,一根根硬邦邦的,朱红油亮,红白相间,香味内敛,便是一道年味十足的美食。我们姊妹仨小馋猫一边数着香肠的根数,一边盼着可以吃香肠的日子。
待到腊味真正上桌,那油光、那香气,仿佛把整个冬天的湿冷都赶到了窗外。年夜饭里,香肠煮熟了,母亲要等它半冷不热的时候才能切片,要不然切不成形。一片片椭圆形的香肠整齐地码在白色的瓷碟里,香味四溢,弥漫在整个屋子里,飘出来的都是父母亲对孩子浓浓的爱意。肥瘦相间的香肠在昏暗的灯光照射下分明闪着晶莹的光,一家人望着香肠,脸上溢满了幸福的笑容。吃一片,细细咀嚼,感到香脆爽口,肥而不腻,满口生香,满满的幸福感。
最佳口味的是,母亲常将香肠整根铺在快熟的米饭上面,溢出的油脂连带着米饭都让人垂涎三尺。一锅饭,一段香肠,吃一口,米饭喷香,瘦肉香而不柴,肥肉糯而不腻,滋味醇香,味道绝佳,足以慰藉饥肠辘辘的胃,独特的烧腊味掺杂着米香,令人欲罢不能。饭后再喝上一碗煮饭期间捞出的米汤,嗝……这舒适度,未曾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的。
我读初三那一年,每个月的月末才能回一次家。食堂的大锅菜表面总浮起无数的油花,吃起来却是味同嚼蜡。香肠是唯一能存放得久的肉类,所以家人们都无私地省下来供给我。但我也幸运地品尝到不同同学家常味的香肠。记忆中永不褪色的画面就是几十个同学三个一伙五个一堆坐在一起吃饭,谁看到他人的碗里没有菜了,就会悄悄地夹一片香肠“支援”对方。即使再寻常的食物也因为这不动声色的互助多了一些别样的情愫。
那时候的沧浪河畔,鱼多,年根岁底就更多,为啥?因为出鱼塘了。每年出鱼塘的日子,那阵子,家家吃鱼,天天吃鱼,连空气里都飘散着鱼的鲜香。
“到了这时候就这么做”的习惯,每年入冬的时候,母亲都要晒腌咸鱼。腌咸鱼不像灌香晒肠那样复杂讲究,母亲只是在盐里拌上八角、茴香、花椒等香料,然后直接擦在鱼身上。腌的最多的是混子鱼(音,青鱼),又叫青混鱼。把青混鱼剁下鱼头,沿脊背剖开后再腌。混子鱼的鱼头和鱼肚子里的鱼泡、鱼籽下锅煮成“鱼泡套”,鲜,香,别有风味。每次腌鱼,最忙的是家里的大花猫,它兴奋地跑进跑出。
鱼在缸里浸了两三天,选一个晴天,穿起来,挂在屋檐下,挂在墙上,挂在院里的树上。那些天,走到哪里都能看到晾晒的咸鱼,那一串串一挂挂的咸鱼成了大街小巷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风吹日晒,两三天后,咸鱼就“冷冷干”(音,家乡方言,要干不干的意思)了。随手折一小截树枝,扒开鱼肚子,撑着继续晒。
数九寒冬,里下河的西北风那叫一个厉害,不几天,就把咸鱼吹干透了,直挺挺硬梆梆的。母亲把咸鱼干收在蛇皮口袋里,扎紧,悬在屋梁上,年前还吃不到它们。你想啊,鲜鱼还吃不完,哪能轮到咸鱼干?吃咸鱼干要到过年后,年货消耗殆尽的时候。不过我嘴馋等不及,隔三差五地背着母亲,拿晾衣叉挑下蛇皮袋,掏条鱼干子放在通红的火叉头上炕着吃,炕熟的鱼干子,咸津津的,酥,脆,香!大花猫鼻子尖,竖着尾巴,喵喵叫着,小鸟依人似的贴着我转圈圈,也想吃上一口。
进入腊月中下旬,家家户户都腌咸猪头过年,故民间有谚语:“有钱没钱,腌个咸猪头过年”。大街小巷挂着的大大小小的猪头,可以说是传统年货的具象标本,这也是最让我欲罢不能的那个咸猪头。在以前正月里饭桌上的各色菜肴中,一碗咸猪头肉几乎是家家待客的必备美食。轻夹一小块入口,咸猪头的“年味”最难忘,满口咸味腊香令人难以割舍,即使被打了耳光说不定也不肯放下。
每年春节前一个多月,父亲凭肉票从肉铺上回来,肩上扛着新鲜的猪头和大块五花肉,那模样就像打了胜仗的将军凯旋,母亲则早已烧好热水,把大缸、粗盐、八角、茴香、花椒等家伙事儿准备妥当。母亲戴上围裙,洗净双手,开始先腌制五花肉。她先将五花肉切成长条,再把盐均匀地抹在五花肉上,手法娴熟,像是在给五花肉估按摩,每一处都不放过。接着,母亲把猪头上的毛发处理干净,猪头上有许多褶子,里面长着毛,难以清除,母亲会用镊子慢慢镊,用刀尖刳,去除猪下腮里的淋巴,清洗干净,沥干水分。然后再用粗盐在猪头两面用力搓擦,每一处都要均匀地搓擦到,使得盐充分接触到猪头的每一个角落。在大缸的底部撒上少许大盐,将猪头和五花肉平放在缸底。腌好后在上面压上一块平整的石头,最后盖上盖子,剩下的就把美味交给时间。过个把星期后,母亲会把腌猪头和五花肉翻个身,并查看缸中卤水是否适中,如果偏少,就将盐开水冷却后倒入缸中,以卤水刚刚漫过猪头和五花肉为宜。经过两个星期的入味过程后,接下来就是清洗晾晒。
母亲会选择晴朗的天气,把浸在缸底的猪头和五花肉拿出来,慢慢清洗,穿上麻绳,挂到院子里晾晒,让阳光照射十日。在冬日阳光的照晒下,肉色由白色慢慢变成绛色,油脂会慢慢往下滴,质地变得越来越硬,皮肉自然风干,离美味越来越近,过年的气氛也越来越浓了。
做腊味是一件慢的事。母亲腌肉三天,晾肉十天,收肉前还要仔细把表面再抹一遍酒,还要翻几次身,检查是否晒得均匀。没有哪个步骤能省略,也没有哪个过程能着急。冬天的滋味,就在这样的等待里慢慢生成。有一次我忍不住问母亲:“这咸猪头和咸肉这么大块,怎么知道哪天算好?”母亲笑得笃定:“风会告诉你。你用手按一下,肉紧了,油亮了,就成了。”
除夕前一天,母亲会把晒干的猪头放在淘米水中浸泡,清除猪头上的灰尘杂质,去掉多余的盐分,清水反复冲洗干净。然后母亲把整只猪头放进大铁锅中,加水漫过猪头,只放点生姜大葱,不放其他任何调料,最大限度保留猪肉的咸香本味。烀猪头是慢工。母亲等大火烧开后便撇去浮沫,改为文火慢慢地烀,这样才能烀得软烂而猪皮不破。那年头,养猪不吃什么精饲料,更不吃摧肥促长的添加剂,肉质紧实,所以烀的时间要长,有句老话叫“火到猪头烂”。灶膛里炉火通红,不大一会工夫,厨房里热气腾腾,肉香也慢慢飘散开来。
母亲烀咸猪头肉时,我们就在厨房守着。平时是贪玩,这时候由贪玩变成了贪吃。鼻孔里随时吸闻着铁锅上木盖缝隙里——香飘益远的咸猪头肉腊香,香气持续不断刺激着蠢蠢欲动的味蕾。等到猪头烀熟冷却后,猪头肉烀得透明,肥肉亮得像一块冻,瘦肉紧得像冬天的风。母亲一边拆着这咸猪头,我在边上不时吞咽着泛出来的口水,见我如此这般的馋相,母亲会往我嘴里塞上一块咸猪头肉,还是热气腾腾的,味香肉美,吃得满嘴流油,大快朵颐。
小时候的年夜饭,好像除夕夜不吃咸猪头肉,就似乎没有长大一岁一样的。我小时候盼吃年夜饭,那时能吃到咸猪头肉,那天还可以放开吃。除夕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对咸猪头开始动眼动耳更动嘴了。老话讲:吃什么补什么。母亲怕我将来眼睛近视,就将猪眼睛连同猪眼眶四周的肉,单独切一块给我吃,可后来我成为家里唯一戴眼镜的大学生;大姐吃东西最挑剔,于是母亲把最“活劲”(兴化方言:口味好的意思)的猪拱嘴那一块给她吃,的确大姐算是我家最“难养”的;母亲也喜欢把猪耳朵那一块给小妹吃,希望她将来要听话,结果得到了验证,小妹是家里最听话的孩子。
与新鲜猪肉做成的红烧肉相比,咸肉切成薄片,整齐地码在白瓷盘里,精的粉红,白的微亮,更是清新。那时候,大蒜炒咸肉是最常见的家常菜。年前年后,巷子里的大蒜混合咸肉的香味总是令我垂涎欲滴,回到家中我能就着一盘大蒜炒咸肉吃掉满满三碗米饭。小时候吃大蒜炒咸肉时,我每次都会把饭倒进菜盘,为的就是享用那浓稠的汤汁,末了还会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过年的时候,母亲总喜欢把咸肉切成方块放进百叶里一起蒸,饭熟的时候,浸满肉汁浓香的百叶就成了全家人最受欢迎的美味了。
快要过年了,眼前又出现小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咸猪头的情景,心里觉得暖暖的。珍馐美味的咸猪头,小时候的味道,也是我记忆里妈妈的味道,一直是我心里过年的味道。身为憨态可掬的猪头,它也许很自豪很开怀吧。爱上咸猪头,因为它们始终能带给我们昔日满满的幸福感!
如今,进入冬天,年过八旬的母亲便容易感冒,支气管炎会引起咳嗽不停。而春节快到了,她还坚持要我去买只猪头,说啥也要再腌上一只猪头,否则,过年时就会觉得缺少点年味。我问她:“外面卖的也不错,你别这么累了。”母亲笑着摇头:“外面卖的是味道。自己做的是心安。”母亲的这句话,让我明白了,冬天的腊味,不只是一道菜,更像是一种人生态度——要花时间,要动手,要懂得等待,也要舍得慢。它不是应付饥饿的食物,而是让人安稳下来的方式。虽说母亲手脚麻利灵敏大不如从前,可仍照老办法吃力地腌上一只猪头,只等除夕烧了来吃了。
往事如烟,家乡腊味的余香仿佛还在唇齿间萦绕。在记忆之中:过年吃上一口母亲亲手灌的香肠,腌的咸鱼、咸肉和咸猪头才有过年的幸福感。而那一串串香肠、一条条咸鱼、一块块咸肉、一个个咸猪头,更像是一种安稳而持久的力量,把冬天裹得厚一些,把生活的味道拉得浓一些。腊味挂在风里,香在风里,甜在心里。
【编者按】这篇散文,以腊味为文字出发点,串联起家乡的烟火气与亲情的温度。从晾晒的香肠、咸肉到母亲制作的细致过程,细节鲜活得如在眼前。家庭记忆中的腊味与母亲的坚守,让腊味不仅是食物,更是乡愁与生活智慧的载体。语言质朴如话,将传统年味与人生态度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读来有岁末的滋味与回味。编辑:穿越中的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