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冲并不遥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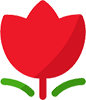 4
4

从1992年第一次去云南开始,32年间我去了彩云之南不下六七次,昆明、德宏、西双版纳,丽江、大理、香格里拉,澄江寒武纪化石群遗址,红河哈尼族的梯田……我都走过。但是直到2024年12月,我才第一次来到慕名已久的腾冲。
之所以迟迟没有去腾冲,主要是因为它交通太不方便,感觉那地方遥不可及。第一次去云南时,分社记者带着我们从昆明开车走滇缅公路到畹町,已经到了腾冲边上的保山,可听说要去腾冲开车至少五六个小时,且山路很不好走,我们只好舍弃。
这一次,我们乘昆明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北京直飞,4小时就到了腾冲。一下子就觉得腾冲不再遥远。
依仗着对腾冲熟得不能再熟的朋友接待,我事先没有做任何功课。到了腾冲,朋友安排去哪儿就去哪儿。倒是一众知晓我到了腾冲的朋友,不断地发微信指点我,应该去这里,应该去那里。
他们都说腾冲的滇西抗战纪念馆必须要看。我们到腾冲第二天,就直奔它而去。恰逢星期天,参观者相当多。
朋友说,滇西抗战纪念馆最早建于1986年,原本比较狭仄。当地有意扩建,却缺乏资金。后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的刘云山来腾冲,看了纪念馆,感觉很有意义,听闻扩建资金有困难,便批示拨专款,新馆才得以在2013年8月15日建成开馆。据说总投资1.5亿元。
纪念馆正厅三面墙上,1300顶不同制式的钢盔呈矩阵式排列,既威武雄壮又别开生面。资料介绍说这些钢盔是当地一位战史迷一顶顶搜集而来,而拍过电视剧《中国远征军》的朋友说,那都是他们用过的道具,捐给了纪念馆。我是既信朋友也不能质疑资料,反正不论这些钢盔来历如何,它们在这个纪念馆,都适得其所。
那次跟分社记者走滇缅公路,也算接触过滇西抗战,但毕竟没有研究,对那段历史一直相当迷糊。这次才算明白了一点: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后,在中国大西南的云南成了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为了输送从海路到东南亚的国际援华物资,1937年底开始紧急修建从昆明到缅甸腊戍的滇缅公路,全长1146.1公里,其中云南境内959.4公里,20万人工9个月建成通车。即使一些路段有原来土路的基础,这速度也相当了不起了。筑路民工牺牲3000多,平均每公里死亡3人,也是血肉铸成的一条公路。
滇缅公路经保山却并不过腾冲,然与腾冲关系密切。后来日军就是沿着滇缅公路打到腾冲的。说起来,这滇缅公路也是好景不长,因为谁也想不到1886年就宣布吞并缅甸并将其纳入自己版图的大英帝国的军队那么不经打。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两个师团1942年1月初开始从缅甸南方发起进攻,两个月就占领了首都仰光,5个月就占领了缅甸全境。这一下,原本是中国抗战大后方的云南,尤其是滇西,突然就成了前线。
日军占领缅甸全境后,在1942年5月3日又沿着滇缅公路侵入到我国畹町,4日即占领芒市和龙陵,眼看就到了怒江边,昆明及整个大西南岌岌可危。5月5日,中国军炸毁了怒江上的惠通桥,凭怒江天险阻住了日军攻势。然而怒江西边的腾冲还是在5月10日落入日军魔爪。
因为一直是后方,估计畹町、芒市、龙陵、腾冲也没什么像样的备战。据说腾冲就是被292名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大摇大摆占领的。不过被占领之后,腾冲一带的抵抗一直不断。特别是以李根源和张问德为代表的一批有家国情怀的腾冲贤达,表现突出。
李根源是辛亥元老,朱德元帅在云南讲武堂的老师。腾冲沦陷后,在昆明担任云贵监察使的李老赶到保山,面对不断轰炸的敌机,争相向东逃命的难民,他镇定地召集各地士绅开会,发表了著名的《告滇西父老书》,号召人们“抱定决心”将敌人驱逐出腾冲、龙陵、滇西国境乃至缅甸,“保住滇西过去历史上的光荣”“在云南抗战史中占最光辉的一页”。
比李根源小一岁的张问德也是民国初年就开始做官的老人,腾冲沦陷后,已经62岁病休归家的张问德被云南省政府任命为腾冲县长。他临危受命,不辞辛劳,率抗日县政府随军转战,流动办公,竭尽全力办理县政,协助军事,锄奸安民。1943年8月31日,在腾冲抗日最艰苦的时候,日军腾越行政班本部长田岛寿嗣致函张问德,企图诱降。张老先生于9月12日回复田岛的《答田岛书》,被誉为当世名檄。他在回函中历数日寇荼毒腾冲人民的种种罪行,严词拒绝其择地会晤长谈的要求,表示自己要竭尽全力使侵略者“终有一日屈服于余及我腾冲人民之前”。两篇文书,一批乡绅,尽显腾冲风骨。
(战前腾冲全景)
收复腾冲的腾冲战役打得很惨烈。从1944年5月11日到9月14日,历时127天。日本人占领腾冲两年,将当初那不设防的小城搞得似乎壁垒森严,让中国军以伤亡1.8万余人的代价,毙敌少将指挥官及联队长以下军官100余、士兵6000余,俘获敌军官4人、士兵60余。一片焦土的腾冲,是抗日战争以来国民党军队收复的第一个有日军驻守的县城。
还有一些细节令人动容。滇缅公路建成后,司机不够,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老先生发布通告号召东南亚华侨有相关技术专长者回国服务,得到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地3200余名华侨的热烈响应,他们短短数月就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洋机工,分9批回国服务,主要承担滇缅公路的运输。他们之中涌现出数位女扮男装的现代花木兰,其中一位李月美,她在一次事故负伤后才被发现是女性,之后她又当护士,继续抗战。
纪念馆还展示了中国远征军在缅北密林中挣扎生存的情景。10万余人的远征军真正在战场阵亡的也就1万多,而4万多人是死在缅北的雨林中,且尸骨无存,仅留下他们的胸章或名牌。
纪念馆毗邻大名鼎鼎的国殇墓园。或者说,滇西抗战纪念馆就是在腾冲国殇墓园的基础上建立的。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编发过云南分社记者采写的关于国殇墓园的对外报道,那可能是改开后我们有关国殇墓园最早的新闻报道。那时没有多媒体,仅凭文字,我还是很难想象墓园的样貌,非常渴望亲眼目睹。不想30多年之后才如愿。
国殇墓园是1944年收复腾冲后,李根源先生提出修建的,以纪念在腾冲战役中阵亡的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将士。墓园1945年1月15日动工,当年7月7日落成。1996年国殇墓园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殇墓园的大门是白族风格牌楼式建筑,门额篆刻“国殇墓园”四字是李根源老所书。
墓园建有忠烈祠,其“河嶽英灵”匾额是蒋介石题书。
忠烈祠后的小团坡上,整齐排列者3346块小方碑,碑上刻着腾冲战役中阵亡将士的姓名和职衔。
此外还有墓墙,刻着9187位阵亡将士的英名。
回到北京后才看到资料说,这里还埋着19名美国盟军将士的亡灵。可惜当时不知道,没有去看。也是有点累,走不动。如果园里有定时的景交车巡回开过,指点游客看这些墓碑,就好了。
我们还是勉力爬上小团坡顶,瞻仰了克复腾冲阵亡将士纪念碑,上有李根源老题写的“民族英雄”四字,以及腾冲会战概要。
在坡顶还看到附近解放后建的革命烈士陵园。
埋有三个日本将领尸体的倭冢,“倭冢”两字也是李老所题。
旁边是痛打日寇的雕像。听说日本人曾提出给腾冲十亿元人民币,迁走倭冢,拆除这个雕像。腾冲拒绝了。
腾冲另一个必去的网红打卡地,就是有600年历史的和顺古镇。
朋友告诉我,和顺是著名侨乡,6000多人口的镇子,在海外的华侨竟有1.2万人,分布在缅甸、泰国、新加坡乃至美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
奇特的是,距腾冲县城不过4公里的和顺,竟未遭日军荼毒。朋友说,和顺有曾经留学日本的先贤,将天皇赐予的宝剑悬挂于通往古镇的牌楼上,阻止了日军进入和顺。总之,这个古镇果真是名副其实,和平安顺安然无恙地幸免于难。
和顺的建筑白墙灰瓦,很有徽派风格。事实上,和顺及腾冲是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最少的地方,汉族人口占比在87%以上,皆因明清两朝从江浙皖等地迁徙了大量军士及其家人来戍边。
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就是和顺人。他的《大众哲学》是引导我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著作之一。我曾经疑惑那样偏远的地方怎么会走出这样一位人物,可是到了和顺,虽然体力原因没有走到艾思奇故居,而一旦发觉这小镇文化底蕴深不见底,我疑惑全消。上个世纪初的腾冲与和顺,得侨乡之便,领风气之先,思想上可能比北京更加开放,与世界更加接近。和顺镇的几位华侨集资于1928年建的图书馆,证明了这种开放。
图书馆就在古镇入口处,位置抢眼。大门上的和顺图书馆几个字,是清末和顺最后一位举人张砺书写,门内“文化泉源”的金字大匾是缅甸瓦城云南同乡会所赠。
进得中式大门,又有一座西式平顶拱形门,上面悬挂着胡适题写的和顺图书馆匾额。
穿过拱门内的小花园,就是图书馆的主楼了,两层五开间砖木结构,两边各有一间带飞檐的角亭,很传统,也很气派。不愧是2006年列为全国重点保护的文物单位。
主楼一层的阅览室,很有历史感。据说和顺图书馆收藏的孤本古籍,省图都比不上。
2008年建馆80周年时图书馆之友赠送的铜铭牌,现在又过了16年了。
主楼后面的藏书楼,很洋气,却与整体建筑风格并不违和。
中国真正的读书人绝不迂腐。和顺图书馆也是一样。这个书香之地1944年曾作为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的临时作战指挥部,为收复腾冲做出了贡献。
图书馆旁边是文昌宫,与图书馆一样彰显着古镇的文化传统。朋友在和顺见过七八十岁挑着担子健步如飞的老人家,不仅识字,还能念出一口流利的英文。
朋友带我们去看弯楼子民居博物馆。沿途经过一条条街巷。每个街巷各有一共同的巷门。
巷门对面,各有一个公共场所,方便巷子里的街坊门休闲或社交。
路经寸氏祠堂,寸是和顺大族,从这讲究的门楼就可以看出这是个很有历史传承的家族。
在滇西抗战纪念馆有寸氏家族寸大进的雕像,他是清末武举人,曾率边地军民多次抗击入侵英军。1942年腾冲沦陷后,88岁的寸大进绝食而亡,尽显民族气节。他有9个儿子,均参加抗战,其中3个儿子为国捐躯。
弯楼子是创办了当地著名商号永茂和的李氏家族的住宅,因其房舍顺着巷道的曲线修建,被乡人形象地称为弯楼子,也体现了李家与邻里的互谅互让。李氏家族兄弟五人,一人早逝,其余四位同甘共苦,亦商亦儒。
他们经商之外,也帮助地方平息匪患,得地方所赠“见义勇为”牌匾。
如今李家族人遍布缅甸、泰国、新加坡、加拿大以及台湾等13个国家和地区,子孙昌盛。
李家的房子坐南朝北,从建筑到家具,都是中西合璧。如这闺楼的小阳台和西式的铁花窗。
走廊落了灰的家具都是古董。
三进三坊一影壁。
供奉着李家祖先牌位的祠堂。
古镇外是一片湿地,因人走进去会陷入水草之中,曾名陷河湿地,又因有野鸭嬉游水上,现名野鸭湖。现在湖边修了码头,游人可买票乘画舫欣赏古镇的水乡风光。
也从水上不同角度看和顺。
和顺让人称道的是,它百年前就已经处于中国的开放前沿,然而却一直保持着其固有的古朴。无论如何大红大紫,却总是低调行事。
村民们依然在河边洗菜。
沿袭多少代的洗衣亭仍然不是摆设,还在使用。
他们还保持着晒干菜的传统,而且镇里一直有给村民们晒干菜的场地。
对比原住民几乎全被外来商家赶走而早看不出自己原本风格的滇北另一古镇,和顺本真的淡定从容才是真美,值得点赞。
腾冲多火山和温泉。这是因为它处于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的冲撞带,地质活动活跃,地下岩浆活动强烈。火山公园需要攀爬,我们自觉爬不上去,就去了热海景区。据说这是腾冲地热显示最集中的地区。
常规的旅游路线要徒步走5公里,也是一路爬山。想想我们没那个体力,只好舍弃了其他景点,只看热海大滚锅。可以乘景交直接到大滚锅下边,爬若干级台阶上去,虽还要爬坡爬台阶,总比徒步上行5公里好得多。
1639年,明代徐霞客曾经来到这里,形容大滚锅“一池大四五亩,中洼如釜,水贮于中,止及其半,其色浑白,从下沸腾。作滚涌之状,而势更厉”。他真是把这大滚锅写得活灵活现,这可能也是大滚锅一名的由来。
我们所见的大滚锅,直径6.12米,水深1.5米,水很清,咕嘟翻滚,热气蒸腾。锅内有三个主要喷水泉眼,出水口温度高达102摄氏度。周围有石栏杆拦着,防止有人会误入滚烫的泉水,那可真是要命的。想想385年前徐霞客来到这里的时候,肯定什么防护设施都没有,那真是危险重重。而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生动完备的记录,确实令人佩服,肃然起敬。
景点有免费为游客自带的鸡蛋蒸熟的服务。
也可以在这里买他们为游客蒸熟的鸡蛋。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云南十八怪之一的鸡蛋用草串着卖。
热海附近的另一个景点,就是佤族村寨司莫拉。这可以说是总书记带红的景点。这个大山中的村子距腾冲县城13公里,是一个有500多年历史的佤族村落,依山而建,有梯田、竹海、湿地、森林。
司莫拉在佤语中的意思是“幸福的地方”。2020年1月,总书记来腾冲考察,只去了和顺和司莫拉这两个地方。估计腾冲也有意扶植司莫拉的乡村旅游,现在凡是腾冲旅游团,似乎行程上都有司莫拉。
而司莫拉也并不让人失望。游客乘景交车穿过森林中开出的公路,一路景色都不错。
到了这个村寨,首先看到他们的田园风光。
还有洗衣沟和水磨坊。
然后步入村子,沿路干净整齐。
有党员挂牌经营的商店。
有游客可以体验做粑粑的作坊。
当年总书记家访过的李发顺家,也成了村里一个网红景点,很多游客慕名而来。
品尝李发顺烤的粑粑,和他或他的家人聊天。粑粑有不同的馅料,我们买了四种,我觉得不错,也有人觉得不怎么好吃。
我们还和李发顺夫妻合影。遗憾的是,我们尝了他家的酸枣糕,感觉不错,一人买了一袋,不想混乱中有人多拿了一袋,在回腾冲的路上才发现这个错误。也不好回去了,便通过微信付款信息查,希望补交货款。却只能找到第三方收款者,无法联系到李家。没有渠道直接沟通,万般无奈,只好通过付款信息显示的“投诉”留言说明情况,希望纠正错误。可是联系了三天,只有语音告知留言,没有处理结果。非常不好意思。希望以后能够再去司莫拉,弥补这个遗憾。
景交不开到村里,所以山上有些景点,我们就上不去了,比如位于村子最高处的佤王府。如果有交通工具解决爬坡问题,我们还可以多看一些地方。
火山脚下的腾冲城固镇江东村,是600年前戍边官兵的营房发展而来,后被误入此地的背包客们发现这个“村在银杏林中,银杏树在家中”的地方景色独特,而以“银杏村”传名于世。甄子丹的《武侠》更为银杏村扬了名。2013年修通了县城直达村里的银杏大道,银杏村成为腾冲又一个旅游打卡地。
11月中是来银杏村观景的最佳时节,我们错过太久,银杏村早已盛景不在。但村旅游公司的讲解员姑娘讲的生动,很让我们涨知识。
她说,银杏村共有万余亩、四万余株银杏,千年以上的银杏就有十余株,百年以上的更有百余株。最老的银杏王,树龄有1300多年,可比这千余户人家的村子更古老。这里的银杏树据信是唐代马帮路经此地遗留的种子长出,很多银杏,包括这棵树王,看似几棵环抱,其实只是一株。
满村黄金甲的时节已过,黄叶却仍有残留。
这里的银杏树大多两抱或三抱。讲解员姑娘说,两抱的是二人相恋,三抱的是添丁进口。
银杏十雌一雄,雄性银杏树都是单一孓然挺立而无合抱,一株雄性银杏树授粉范围可达三、四平方公里。
银杏村距离火山很近,村里人家的围墙都是火山石。
在腾冲,我们认识了创立于1994年的恒益集团和其老总段治葵。这个老总和这个企业似乎很低调,出了腾冲好像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经朋友安排住在他们家的东湖温泉康养酒店,才初步了解了这个企业。
康养是恒益集团近几年开始发展的一个新事业。守着腾冲的旅游资源和众多温泉,恒益做康养可谓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他们并不像目前很多以“康养”为号召的企业,仅凭环境加酒店就等于康养,而是非常认真地经营康养。他们的理念是“以生活方式和非医疗干预改善生命健康”,我对这点非常欣赏。
他们不仅有温泉,有国内外引进的各种辅助康养的先进设备,也不仅有教授太极拳、八段锦或瑜伽等各种健身的项目,还有一个中西医结合的专家团队,可以针对不同体质和慢性病人的情况,提供不同的康养康复套餐。此外他们还有康养研究中心。这样认真做康养的企业,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我们参观了恒益集团在滇滩镇的大黑山中草药基地。位于高黎贡山下的腾冲四季和煦,雨量充沛,森林覆盖率达77%,是云南省中草药资源最丰富的地区,自明代就有种植中草药的传统。恒益集团的中草药基地2017年开建,租当地农民两千亩地,种植腾冲本土生长的350多种中草药,并在以每天80到100元的标准雇佣当地农民临时工的基础上,向他们免费提供种子和种植技术,统一收购,收入和农户四六分成,帮助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我们参观了他们的百草园中草药科普园地。他们主要种植黄精,但是目前刚收获完,地上空空的。
记录了一些名字听上去挺新鲜的药草。如开口箭。它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可治疗咽喉肿痛,外用还可以治疗毒蛇咬伤。
朱砂根。有解毒消肿,活血止痛,祛风除湿之功效。
十大功劳。主治细菌性痢疾,急性肠胃炎,传染性肝炎,肺炎,肺结核,支气管炎,咽喉肿痛。
我们这几天都吃过的香橼果的树原来长这样,这些香橼果树6年了还末到果龄。
中午在基地吃中药膳,极美味。餐前主人招待我们吃当地特色的烤小耳朵猪,简直不要太鲜美。这种小耳朵猪最大也就长四五十斤,那烤出来的味道乳猪可是比不了。我们大快朵颐,没想到这还只是前菜。
恒益集团农业产业的另一个大项目东山草原牧场,已经成为横冲的另一个打卡景点。牧场面积有2.2万亩,在海拔2300米的山上。他们引进国外优质品种的肉牛经过几代培育,发展出他们自己的品种云岭牛,肉质非常鲜美。
在东山,他们还修了一条全长7公里的彩云栈道,我们走了其中几百米,欣赏腾冲高黎贡山的美景。
远眺腾冲最具标志性的休眠火山打鹰山。
游览高山上的人工湖。
还有正在建的帐篷酒店。
当时主人没有介绍。我回来之后才了解到,这地方原来基本上是荒山,草原覆盖率不超过40%。他们经过几年的草种繁育、人工种草,草原覆盖率已提高到95%。好山好水好空气好牧草,云岭牛当然好吃。
事后还了解到,我们看的中草药种植业,是恒益集团农业产业的“一颗草”,这东山牧场是他们的“一头牛”,他们的农业还有“一朵花”,就是他们6000亩的玫瑰庄园,主要种植大马士革玫瑰等1400个玫瑰品种,包括玫瑰产品加工,年产值3亿多。此外还有“一条鱼”,就是三文鱼的繁育、养殖、加工和销售。这三文鱼我们尝过,极鲜且绝对无污染。
资料还说,2024年恒益集团位列云南企业百强第55位,云南高新技术企业百强第26位,云南服务业企业50强第15位,云南非公企业百强第37位。
腾冲不产玉,但据说是最早发现翡翠价值的地方,所以有“玉出腾越”之说。腾冲的每一条街道,每一片土地似乎都与翡翠息息相关。距酒店不远,有一个翡翠博物馆,据说是中国唯一的一家翡翠博物馆。这是段总个人在2014年创建的。段总并不做翡翠生意,他最早做铁矿起家,长年往来缅甸,收藏了不少翡翠。作为一名腾冲人,他认为腾冲既然是“中国翡翠第一城”,是翡翠文化的发祥地,就应该有一座属于自己城市的翡翠博物馆。
博物馆既普及各种翡翠的知识,也厘清了腾冲承载的翡翠文化历史,包括腾冲作为翡翠贸易集散地的历史风貌。
这并非翡翠珍品,只是用它表示翡翠是玉中之王,所以放在宝座上。
这是段总2009年在缅甸竞拍到的一块翡翠石,重24吨,世界纪录协会经过一系列严格复杂的认证程序确认它是世界最大的翡翠毛石,因此号称世界翡翠之王,花了一年半时间才运回腾冲。
从这块翡翠毛石上切下的一片。
翡翠浮雕四大名楼桌屏之一的鹳雀楼,真是漂亮。
原石花纹。
早年工匠拉丝解玉的情景。
自古以来,腾冲位于滇缅贸易的交通要冲,是古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腾冲人下南洋,开矿做生意,离不开马帮这古老的物流手段。所以腾冲也被称为称马帮驮来的古镇。我们事先没有准备,对腾冲的马帮文化很陌生,只是通过两个餐馆与腾冲马帮文化有了肤浅的接触。
一个是侨香斋。朋友说腾冲的稀豆粉很有名,上过《舌尖上的中国》,带我们去品尝。想来是小吃,我以为应该去个街边店吧。没想到他带我们到了一个看上去挺深小巷。后来知道这是在腾越镇的闫家塘。
一个古色古香的大门上写“侨香斋”三字。原来是一位张姓马帮主的旧居。
正房。还有好几进院子。都是古色古香的样子。
宽大的后院。
棚子里有磨豆粉的老石磨。他们家的稀豆粉,菌蛋羹,腊肠,豌豆苗豆腐汤,鲜香美味令人回味。
不想朋友又带我们去了更为气派的马帮大院。大院门脸小小的,完全看不出内里乾坤竟那么大。
和侨香斋不同,马帮大院过去还真是马帮驿站,据说建于清末民初,至今还保留这明清的建筑样式,又有当地的建筑特色。
马帮大院门口以及里面的一些陈列室,挂着不少当年马帮的老照片。
进入大院之后有好几进院子,一条又窄又长的甬道的侧墙上还有马帮的浮雕。
茶马古道的牌坊。
牌坊背后的门额上写着“走夷方”三字,感觉很有意味。他们不说“走四方”,而是“走夷方”,目标真是很明确。
还有当年马帮的用具陈列。
割舍不掉的马帮文化。
还有花园。
腊肉琳琅。
我后来才知道,这马帮大院就在腾冲的绮罗古镇,也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小镇。徐霞客385年前来腾冲,停留40天,主要就住在下绮罗村一个李姓人家。那老宅现在还在,可惜我们不知道,错过啦。
腾冲是徐霞客西行所到最远的地区,也是他晚年最后考察的一个地方。想想那个时候没有火车更没有飞机,连汽车都没有,他从中原到云南跨越千山万水已是不易。进入云南,还要翻越云岭、怒山、高黎贡山;横渡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所以说他称腾冲是“极边第一城”,完全有可能。
如今,现代高效的物流取代了马帮,腾冲离我们不再遥远。因此,尽管这第一次的腾冲之行有许多未到之处,我却也并不遗憾。腾冲,我们还会再来的。
【编者按】文章以作者32年云南游历为铺垫,聚焦2024年末首访腾冲的旅程,串联起这座“极边第一城”的多重面孔:滇西抗战纪念馆里1300顶钢盔诉说着血色历史,国殇墓园的碑刻铭记着远征军的牺牲,拒绝日方迁走倭冢的坚守更显民族风骨;和顺古镇以600年侨乡底蕴、中西合璧的建筑与活态的市井日常,诠释着“和平安顺”的真谛;热海大滚锅延续着徐霞客笔下的沸腾,司莫拉佤族村藏着乡村振兴的活力,银杏村与恒益集团的康养、农业产业则展现着腾冲的多元魅力。从交通阻隔的往昔到4小时直飞的如今,作者用脚步丈量腾冲的历史纵深与当下生机,字里行间满是对这片土地的敬畏与喜爱。腾冲是座用历史与当下交织成的城。它既守着民族气节的底色,又在康养、产业发展中焕发新生,让人读懂“极边”之地的厚重与鲜活。推荐阅读赏析!编辑:攀登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