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沙岗的秋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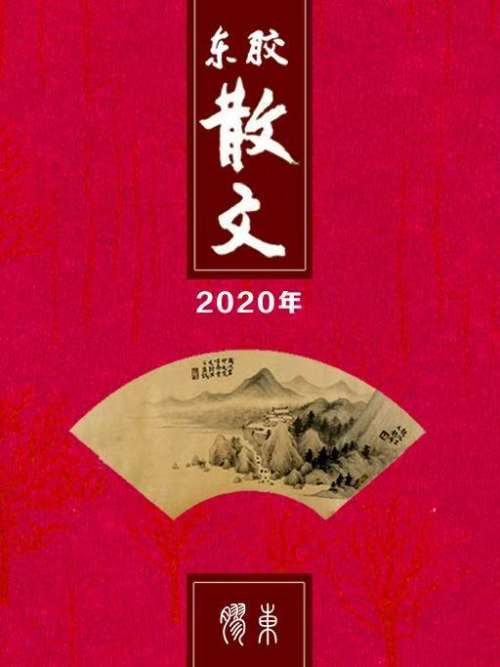
走在车水马龙的城市街道上,飒爽的秋风裹挟着一丝丝香甜,迎面拂来。循着扑鼻而来的味道望去,十字路口的一角,一个手戴皮手套烤地瓜的人,在圆铁桶内取地瓜、称地瓜、收钱,忙得不可开交。久违的香甜味道,勾起了我对故乡大沙岗秋收的回忆……
地瓜,鲁西南人俗称“红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物质十分贫乏的年代,那时也正是兴生产队时期,地瓜几乎是庄稼人的主食。
张庄村西边是一片大沙岗地,足有八十余亩,归俺四队所有,是种植地瓜的最佳墒地,长出的地瓜个头大,淀粉多,煮着吃又甜又面,深受社员们的喜爱。
金秋十月,天高云淡。中秋节前后是地瓜收获的季节。东方刚露鱼肚白,村西大柳树下的铃声便唤醒了社员们,大家拿着抓钩、镰刀和耙子等工具,男女老少齐聚大沙岗。望着墨绿色秧蔓覆盖的田野,人们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欢声笑语回荡在大沙岗上空。
这时,高个子张队长亮开了他的大嗓门:“妇女割秧,男劳力刨红薯,老头老太太拾红薯!”一声令下,妇女们挥镰如风,刀落蒂断,白生生的浸液从蒂端溢出。只见地瓜把堌堆拱得一道道指巴宽的裂缝,长势喜人,人们赞叹,又是一个地瓜丰收年。男劳力挥起抓钩与地下的地瓜来了个“亲密”接触,一个个红润润的地瓜从沙土中被搂了上来,一垄垄的惊喜,接受着社员们的“检阅”,丰收的喜悦挂在每个人的笑脸上。人们感恩大沙岗,是大沙岗肥沃的土地和丰盛的馈赠,养育了一代代年轻的后生。
下午,是生产队分地瓜的时候。身材魁梧的张队长是“总指挥”,吩咐生产队记工员负责看称,会计负责记账,让两个虎背熊腰的壮汉抬大箩筐。在那个“缺工缺粮”的年代,记得地瓜是按人口和工分分配的。分完一家,会计高喊着户主的名字和斤数,然后把写好名字的小纸条压在地瓜堆上。因俺队人口多,地瓜常常要分到太阳落山才能“收姜维”。
接下来,是大沙岗最为紧张和热闹的时刻——擦地瓜和摆地瓜片。大沙岗成了沸腾的秋收“战场”,大人们吆三喝四、呼儿唤女乱作一团,男人们在自家地瓜堆旁“吭哧吭哧”地平地。妇女们拿着地瓜在擦子上面上下飞动,老头、老太太和孩子们忙着摆地瓜片。顿时,大沙岗响起此起彼伏的“嚓嚓”声,雪白的地瓜片在人们家常里短的说笑中慢慢扩展着“领地”。有时人们披着朦胧的月色奋战,有时挑着“马灯”加班。田野里秋虫鸣叫着不眠之夜,夜空里的星斗眨巴着神奇的眼睛,不觉间露水打湿了衣衫,方知已是深夜。
有时,放学后的我,深一脚浅一脚来到大沙岗,帮母亲摆地瓜片。摆地爪片也是件苦差事,蹲在地上时间一长会腰酸腿疼,站立时会头晕脑胀,两只眼只冒“金星”。吃不消的我,往往嚷着母亲尽快“收工”,还好,有左邻右舍出手帮忙,提早结束了“战斗”。
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那时节,就怕秋雨来“造访”,特别是晚上,一旦从小广播喇叭听预报有雨,社员们便立刻慌了神,生怕到手的瓜干被雨淋,一季的收成被泡汤。虽然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但去往大沙岗的羊肠小道上早已灯火点点,手电筒在路上照来扫去。有拉地排车的,有拿包袱、麻袋的,也有扛耙子的,人们风风火火地往大沙岗赶。抢收瓜干的场面尤为壮观。男女老少在大沙岗打响了抢收“战斗”,大家手忙脚乱地搂的搂,捡的捡,麻袋里装,床单里倒,一门心思赶在下雨前把维持生计的口粮抢回家,往往抢收到大半夜,尽管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但想到家里地瓜还得抢收,于是,心急火燎的人们又大步流星地往家赶……
光阴荏苒,一晃五十余年过去了,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人的生活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如今的大沙岗上矗立起一排排教学楼,盈耳的是琅琅的读书声。可是,我仍然怀念昔日的大沙岗,怀念它曾经馈赠给我们的香甜地瓜,更难忘与地瓜结缘走过的艰难岁月。
【编者按】秋风里飘来的烤地瓜的香,让作者回想起家乡大沙岗的红薯秋收的景象,那时由于物资匮乏,红薯被当成主梁,大沙岗每逢红薯秋收,男女老少齐上阵,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这篇文字我们看到过去秋收久违的热烈场景,快乐是那么直接和简单,虽然不富足,但对美好生活热诚的渴望却让人难忘。推荐阅读。编辑:梁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