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笔记之二百六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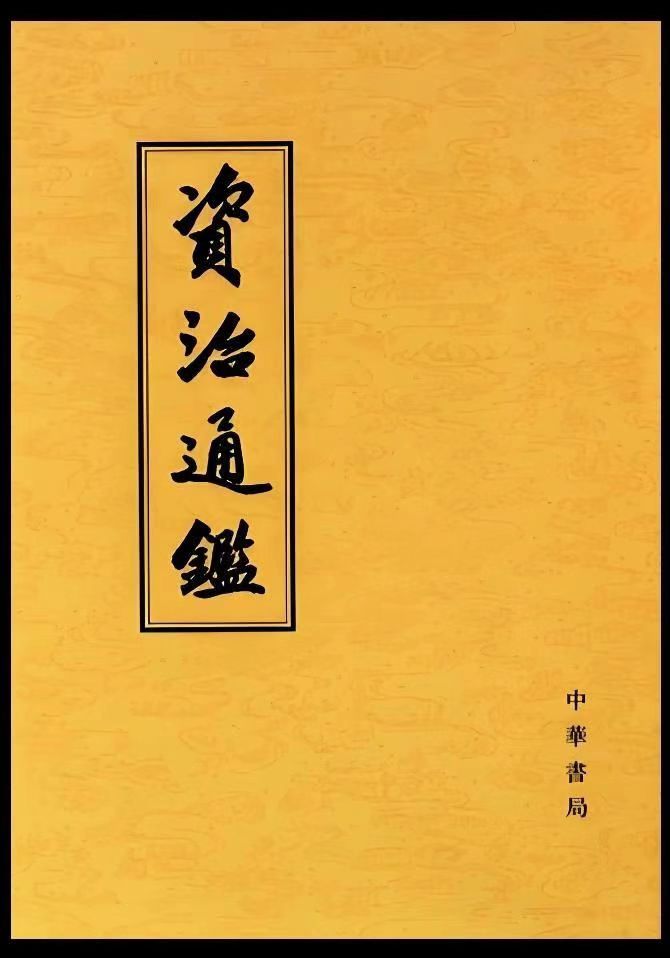
在《资治通鉴》中,讲了很多君王和贤臣的为政之道。贤臣应以“务实、谦逊、尽职”作为为政的核心,而君王则要善于识别臣属,讲求用人之道。这样才能确保政权的稳固。《资治通鉴》卷二十五记载了汉宣帝时期的一些事件,阅读这些文字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发。原文如下:
魏相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相敕掾史按事郡国,及休告,从家还至府,辄白四方异闻。或有逆贼、风雨灾变,郡不上,相辄奏言之。与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辅政,上皆重之。
丙吉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孙遭遇,吉绝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会掖庭宫婢则令民夫上书,自陈尝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问,则辞引使者丙吉知状。掖庭令将则诣御史府以视吉,吉识,谓则曰:“汝尝坐养皇曾孙不谨,督笞汝,汝安得有功!独渭城胡组、淮阳郭征卿有恩耳。”分别奏组等共养劳苦状。诏吉求组、征卿;已死,有子孙,皆受厚赏。诏免则为庶人,赐钱十万。上亲见问,然后知吉有旧恩而终不言,上大贤之。
帝以萧望之经明持重,议论有馀,材任宰相,欲详试其政事,复以为左冯翊。望之从少府出为左迁,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闻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谕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之于三辅,非有所闻也。”望之即起视事。
初,掖庭令张贺数为弟车骑将军安世称皇曾孙之材美及征怪,安世辄绝止,以为少主在上,不宜称述曾孙。及帝即位而贺已死,上谓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称我,将军止之,是也。”上追思贺恩,欲封其冢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贺有子蚤死,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与上同席研书指,欲封之,先赐爵关内侯。安世深辞贺封;又求损守冢户数,稍减至三十户。上曰:“吾自为掖庭令,非为将军也。”安世乃止,不敢复言。
上心忌故昌邑王贺,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令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毋下所赐书。敞于是条奏贺居处,著其废亡之效曰:“故昌邑王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行步不便。臣敞尝与之言,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邑多枭。’故王应曰:‘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臣敞前言:‘哀王歌舞者张脩等十人无子,留守哀王园,请罢归。’故王闻之曰:‘中人守园,疾者当勿治,相杀伤者当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罢之?’其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如此。”上乃知贺不足忌也。
这段话的白话文意思是,魏相喜欢研读汉朝的旧事和有利于国家的奏章,多次整理汉朝建立以来对国家有利的举措,以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的建议,上奏请求朝廷施行。他还告诫下属官吏到各郡国查办事务时,以及休假从家中返回官府时,要立刻汇报各地的异常情况。有时地方上发生叛乱、风雨灾害,郡国不向朝廷上报,魏相就会主动上奏说明。他和御史大夫丙吉同心协力辅佐朝政,汉宣帝对两人都很器重。
丙吉为人深沉宽厚,不夸耀自己的功劳。自从汉宣帝(曾孙)即位后,丙吉绝口不提过去自己对宣帝的救助之恩,所以朝廷中没人知道他的功劳。恰逢掖庭宫婢“则”让她的丈夫上书,自称曾对宣帝有抚养之功,奏章下交掖庭令查问,“则”的供词牵连出使者丙吉,说丙吉知道实情。掖庭令带着“则”到御史府见丙吉,丙吉认出了她,对她说:“你曾经因为抚养皇曾孙不细心,我还责罚过你,你哪来的功劳!只有渭城的胡组、淮阳的郭征卿才对皇曾孙有恩。”丙吉还分别上奏了胡组等人共同抚养皇曾孙的辛劳情况。汉宣帝下诏让丙吉寻找胡组、郭征卿,两人已经去世,他们的子孙都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宣帝又下诏将“则”免为平民,赐钱十万。宣帝亲自召见丙吉询问,才知道丙吉过去对自己有恩却始终不提及,非常敬重他的贤德。
汉宣帝认为萧望之通晓儒家经典、行事稳重,议论政事有见地,有担任宰相的才能,想详细考察他处理政务的能力,就又任命他为左冯翊。萧望之从少府调任左冯翊,觉得是被贬官,担心自己不合宣帝心意,就上书称病请假。宣帝听说后,派侍中成都侯金安上向他传达旨意:“我任用官员,都会让他们先治理百姓来考察功绩。你之前担任平原太守的时间很短,所以让你在三辅地区再历练一下,没有别的意思。”萧望之于是起身任职。
当初,掖庭令张贺多次向弟弟车骑将军张安世称赞皇曾孙的才能和异常禀赋,张安世总是阻止他,认为当时年轻的汉昭帝在位,不应该过分称颂皇曾孙。等到宣帝即位时,张贺已经去世,宣帝对张安世说:“掖庭令生前常称赞我,将军当时阻止他,是对的。”宣帝追念张贺的恩情,想追封张贺的坟墓为“恩德侯”,设置二百户人家守护坟墓。张贺有个儿子早年去世,他的继子是张安世的小儿子张彭祖。张彭祖小时候还曾和宣帝一起读书,宣帝想封张彭祖为侯,先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张安世坚决推辞追封张贺的事,又请求减少守护坟墓的户数,最终逐渐减到三十户。宣帝说:“我是为掖庭令(张贺)这样做,不是为将军(你)。”张安世才不再推辞,不敢再提反对意见。
宣帝心中忌惮前昌邑王刘贺,赐给山阳太守张敞盖有玺印的诏书,让他谨慎防备盗贼,监视往来的过客,并且要求不要把诏书的内容泄露出去。张敞于是逐条上奏刘贺的居住情况,以及他被废黜后毫无起色的表现:“前昌邑王刘贺,肤色青黑,眼睛很小,鼻尖尖而低,胡须眉毛稀疏,身材高大,患有风痹病,走路不方便。我曾经和他交谈,想试探他的心思,就用不祥的鸟暗示他说:‘昌邑地区有很多枭鸟。’刘贺回答说:‘是啊。以前我向西到长安时,根本没有枭鸟;后来回来,向东走到济阳时,才又听到枭鸟的叫声。’观察刘贺的衣着、言语、举止,他轻狂而不明事理。我之前上奏说:‘已故昌邑哀王的歌舞艺人张脩等十人没有子女,一直留守在哀王的墓园,请求让他们回家。’刘贺听后说:‘宫中的人守墓园,生病的就别医治,互相杀伤的就别追究,想让他们快点死。太守为什么要让他们回家呢?’他天生喜好混乱败亡,始终不懂得仁义,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宣帝这才知道刘贺不值得忌惮。
这段话蕴含着一些道理。首先是贤臣的为政之道。魏相注重借鉴历史经验、倾听地方实情,丙吉宽厚低调、不邀功,两人“同心辅政”,体现了贤臣“务实、谦逊、尽职”的为政核心。治理国家需依托过往经验、关注民生疾苦,且身居高位更要戒骄戒躁。
其次,君主的识人与考察也很重要。汉宣帝对萧望之“先考察再任官”,既认可其才能,又通过实际政务检验其能力。对丙吉则“亲问而知其恩”,不被表面信息误导,展现了君主“知人善任、注重实绩、深入体察”的用人智慧。
第三,臣子的分寸与忠诚十分重要。张安世阻止兄长称颂皇曾孙,是为维护朝堂秩序,用以避免“少主在位时称颂旁支”的嫌疑。后来宣帝追封张贺,他又“辞封减户”,既不贪功,也不违逆君恩,体现了臣子“守分寸、明大局、不越权”的忠诚之道。
第四,对“潜在威胁”的理性判断十分必要。宣帝起初忌惮刘贺,但通过张敞的细致观察与奏报,确认刘贺“轻狂不惠、无谋无德”,最终放下忌惮,说明治理中需“以事实为依据,不凭主观猜忌判断威胁”,避免不必要的内耗。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编者按】以史为镜见兴衰,以人为鉴知得失。鉴往知来,贤臣以务实谦逊辅政;明察笃行,明君以识才察绩安邦。汉宣一朝君臣相得之智,恰是《资治通鉴》治国理政的精要注脚。推荐阅读赏析!编辑:攀登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