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笔记之二百六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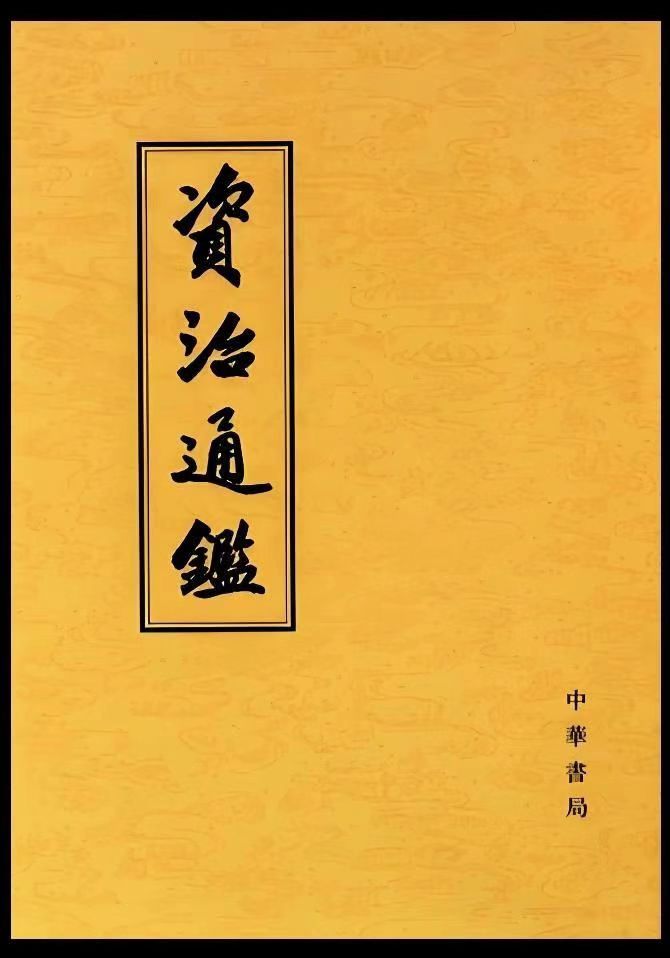
如何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是统治者需要考虑的问题。汉宣帝汲取了汉朝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内部治理和对外关系上采取了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资治通鉴》卷二十五记载了一些事件,值得思考。原文如下: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元康二年
春,正月,赦天下。上欲立皇后,时馆陶主母华婕妤及淮阳宪王母张婕妤、楚孝王母卫婕妤爱幸。上欲立张婕妤为后;久之,惩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更选后宫无子而谨慎者。二月,乙丑,立长陵王婕妤为皇后,令母养太子;封其父奉光为邛成侯。后无宠,希得进见。
五月,诏曰:“狱者,万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奏不如实,上亦亡由知,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如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又曰:“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其更讳询。”
匈奴大臣皆以为“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由是数遣兵击车师田者。郑吉将渠犁田卒七千馀人救之,为匈奴所围。吉上言:“东怀去渠犁千馀里,汉兵在渠犁者少,势不能相救,愿益田卒。”上与后将军赵充国等议,欲因匈奴衰弱,出兵击其右地,使不得复扰西域。
魏相上书谏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以动兵。‘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风俗尤薄,水旱不时。按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于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上从相言,止。遣长罗侯常惠将张掖、酒泉骑往车师,迎郑吉及其吏士还渠犁。召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以郑吉为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
这段文字的意思大致是这样的,汉宣帝(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
春季正月,汉宣帝大赦天下。宣帝打算册立皇后,当时馆陶公主的母亲华婕妤、淮阳宪王的母亲张婕妤、楚孝王的母亲卫婕妤都深受宣帝宠爱。宣帝原本想立张婕妤为皇后;但过了许久,他吸取了霍氏(霍光家族)曾试图谋害皇太子(刘奭,生母早逝)的教训,于是改选后宫中没有子嗣且行事谨慎的嫔妃。二月乙丑日,宣帝册立长陵人王婕妤为皇后,命她以母亲的身份抚养皇太子;同时封王皇后的父亲王奉光为邛成侯。王皇后不受宠爱,很少有机会觐见宣帝。
五月,宣帝下诏说:“刑狱关系到万民的性命。能让受刑后存活的人不怨恨,被判死刑的人不遗憾,这样的官吏才能称得上是合格的文官。但如今却不是这样,有的官吏运用法律时心存狡诈,曲解律条、玩弄手段,量刑轻重不公,上报的案情也不符合实际,我又无法一一知晓,天下百姓还能依靠什么呢!各郡国二千石级官员(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要仔细考察下属官吏,不得任用这类人。还有的官吏擅自征发徭役,整治驿站的饮食车马,刻意讨好过往的使者宾客,超越职权、违反法令来博取声誉,这就像踩着薄冰等待太阳出来,随时可能崩塌,难道不危险吗!如今天下多地遭受瘟疫灾害,我非常怜悯受灾百姓,命令各郡国中受灾严重的地区,免除今年的租赋。”
宣帝又下诏说:“听说古代天子的名字,难认且容易避讳;从现在起,我的名字‘病已’改为‘询’(即刘询)。”
匈奴大臣都认为“车师(西域国名)土地肥沃,靠近匈奴,如果让汉朝占据这里,大量开垦田地、囤积粮食,必定会危害我国,不能不争夺”,因此多次派兵袭击在车师屯田的汉朝士兵。汉朝使者郑吉率领渠犁(西域国名,汉朝在此屯田)的七千多名屯田士兵前去救援,却被匈奴军队包围。郑吉上奏宣帝说:“东怀(地名)距离渠犁有一千多里,汉朝在渠犁的士兵人数少,按形势无法前去救援,希望增派屯田士兵。”宣帝与后将军赵充国等人商议,打算趁匈奴国力衰弱,出兵攻打匈奴的右部地区,让它无法再侵扰西域。
魏相(当时任御史大夫,后任丞相)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平定叛乱、诛杀残暴之人,这样的军队叫‘义兵’,率领义兵的人能成就王业;敌人主动侵犯自己,不得已才起兵反抗,这样的军队叫‘应兵’,率领应兵的人能取得胜利;为小事争怨、忍不住愤怒而起兵,这样的军队叫‘忿兵’,率领忿兵的人会失败;贪图别人的土地、财物而起兵,这样的军队叫‘贪兵’,率领贪兵的人会全军覆没;依仗国家强大、自夸人口众多,想向敌人炫耀威势而起兵,这样的军队叫‘骄兵’,率领骄兵的人会亡国。这五种情况,不只是人为因素决定的,更是天道规律。近来匈奴曾有善意,俘获的汉朝百姓,都会送回来,没有侵犯汉朝边境;虽然争夺车师的屯田之地,也不值得让我们大动干戈。如今听说各位将军想发兵攻入匈奴境内,我愚昧地不知道这支军队该归为哪一类!现在边境各郡贫困匮乏,百姓父子共穿一件用狗羊皮毛做的衣服,吃野菜野果,常常担心无法生存,很难再调动他们参军作战。‘战争之后,必定会有灾荒之年’,这是说百姓的愁苦之气会破坏天地间阴阳的和谐。出兵即使获胜,也会有后续的忧患,恐怕灾害变故会因此发生。如今各郡国的太守、诸侯国的相,很多是不称职的人选,社会风气尤其浅薄,水旱灾害频繁发生。据统计,今年子弟杀害父兄、妻子杀害丈夫的案件共有二百二十二起,我愚昧地认为这不是小的变故。现在陛下身边的大臣不担忧这些,却想发兵向远方的夷族报复微小的怨恨,这恐怕就像孔子所说的‘我担心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小国名),而在自己的宫廷之内啊’。”
宣帝听从了魏相的劝谏,停止了出兵计划。派遣长罗侯常惠率领张掖、酒泉两郡的骑兵前往车师,迎接郑吉和他的官兵返回渠犁。召回原本在焉耆(西域国名)的前车师太子军宿,立他为车师王;将车师国的百姓全部迁徙到渠犁居住,于是把车师原来的土地让给了匈奴。任命郑吉为卫司马,派他负责守护鄯善以西的南路地区。
汉宣帝总结了汉朝以前的经验教训,在立后问题上采取审慎的态度,以“稳”为先,从而规避政治风险。汉宣帝放弃宠妃张婕妤,选择无子且谨慎的王婕妤为后,核心是吸取霍氏乱政、谋害太子的教训,避免“母凭子贵”引发后宫与外戚专权,优先保障皇太子的地位稳定,体现了他在皇权继承问题上“重大局、轻私情”的政治理性。
汉宣帝认识到。治吏与民生:刑狱公平、轻徭薄赋是治国根本。宣帝针对吏治弊端下诏,强调“刑狱关乎万民性命”,禁止官吏曲解法律、擅兴徭役,同时免除灾区租赋,本质是通过规范权力、体恤民生来巩固统治基础——深知“民为邦本”,只有官吏清廉、百姓安定,国家才能稳定。
在对外政策方面,汉宣帝反对“忿兵”“贪兵”,坚持务实克制。他接纳了魏相提出的“五兵之说”(义兵、应兵、忿兵、贪兵、骄兵),放弃攻打匈奴,并非软弱,而是认清“边境贫困、内有灾变”的现实,避免因“争小利、泄私愤”发动非正义战争,也就是忿兵和贪兵,体现了“先安内、后攘外”的务实外交策略,也印证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用兵需符合天道与民生的原则。
这段话要有防患于未然:警惕“萧墙之祸”,重视内部问题的意思。魏相以“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警示宣帝,指出“子弟杀父兄、吏治腐败、灾害频发”等内部问题远比匈奴争地更危险,提醒统治者不可忽视内部矛盾而盲目对外用兵。这一观点贯穿中国古代治国理念,即“内治清明”是抵御外患的根本。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编者按】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汉宣之治,藏于审慎与务实之间。立后避外戚之祸,治吏固民生之本,对外弃忿兵之念,皆为长治久安计。魏相“萧墙之祸”的警示,更道破治国核心:内治清明方为御外之基,防患未然远胜事后补救。推荐阅读赏析!编辑:攀登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