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撒谎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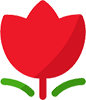 10
10

那年,记不清是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反正我们能熟练背诵“备战备荒为人民”了——就结束了下午的玩耍岁月,开始有定量地积肥(俗称捡粪)了。因为就我们的实力,“备战”挨不上边儿,那是民兵们的事。“备荒”能挨上边儿,因为那就是要多打粮食,而要想丰收,粪肥必不可少(那时候还没使用化肥,甚至连名儿都没听过)。老师教导我们:“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所以需要我们共产主义接班人去积肥。她作为一个知识青年,那谚语也是现学现卖给我们,但我们信服,牢记在心,跃跃欲试,为班级争光,为学校争光,为“备荒”出力。
于是,上午的课程一结束(那时候半天课),下午我们就左手一个菜篮子,右手一个粪筐,一边给自家的猪寻找野菜食粮,一边为学校、为生产队的庄稼积攒肥料。当然,最后都是为国家、为革命做贡献。
那时候,我们的教室是一排平房,每间教室有三个窗户,窗台很高,下面风景独特:总有二三十个臭烘烘的空粪筐堆在那里。当时规定每人两天上交一筐,早晨到校,由一个老校工核查计数,然后倒到学校的大粪堆上,空筐放到窗台下面,老师上班再清点一遍。夏季因为容易发酵,味道太大,所以只在其他三个季节来做,但除了冬天,味道还是足以弥漫。
可是,久而久之,田野里、马路上的粪肥就不够缴纳任务了,因为生产队的牲口数量是固定的,捡粪的学生越来越多。于是我们男生就结伴往远处走,走到荒僻的田间作业路,虽然劳动量大很多,但能勉强凑够数。女生胆小,不敢离家太远,往往完不成任务,经常被老师训得哭哭啼啼。
后来,我们发现,女生不怎么哭了,原来上交数量大体达标了。奥秘在于好几个手巧的家长,给自己的孩子特制了粪筐。那筐有的直径小了很多;有的直径不变,但深度几乎没有了,呈平底状,就像现在饭店里的盘子,容量也就正常的三分之一。不长时间后,有些男生也用上了小筐。那个时候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没人敢私自买卖,不然的话,这种“学生筐”一定是抢手货,绝对的“私人订制”版。
转眼到了寒假,老师规定了假期积肥数量,并且嘱咐我们,如果交的时候校工不在,一定要有其他人证明才能算数。几十年前的东北,数九隆冬时节,凌晨温度多在零下三十度以下,我们都直接体会过“滴水成冰”:吐出的唾沫掉地上就是一块冰疙瘩。但我们必须早早起床,因为冬天出动的马车牛车太少了,稍晚一点就一天没有收获。当年,我们的棉衣远不如现在的羽绒服、皮大衣保暖,就是普通的棉袄棉裤,有的还很破旧。那时小孩子多数是穿不起衬衣衬裤的,穿法俗称“空心棉”,就是光溜溜的套上棉衣棉裤。但遵照一句俗语还是解决一点问题的:皮棉三层,不如腰间一横。我们“腰间一横”一根麻绳,果真暖和许多,可还是有好多人手上留下冻疮。即使这样遭罪,收获还是很少。
这时候拴柱最让人羡慕了,他爷爷是生产队的饲养员,他偶尔会从队里的马厩里刨出来马粪,只是有的块儿太大,冻得实,来不及打碎,被人识破了几回,就前功尽弃了。其实更让人羡慕的是我的堂姐和堂妹,她俩是城里人,每年假期都来我家,躲过“学工”的任务,说是下乡“学农”,每天在我家一觉睡到大天亮,醒了就随便玩儿。开学前夕,在我们生产队随便开一个劳动证明,拿回学校一切都搞定,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立志当一个城里人。
春节过后,年味儿淡去,开学在即。积肥筐数不够,抓耳挠腮,一筹莫展,连哥儿几个在一块儿玩儿,都兴趣寡淡。一天,邻居家铁二哥凑近我问:
快开学了,筐数够没够啊?
唉,还差一半儿呢。我有点沮丧。
我也不够,要不——我给你证明你交够了,你再给我证明啊?
这——行么?老师知道该批评了。我有点儿动心,又有点儿胆怯。
没事,我班同学以前都是这么互相证明的,好使、管用。咱俩不是一个班的,证明起来,老师容易信。他口气坚定,信心十足。
那——好吧。想想每天起早挨冻,有时候筐里还空空如也,我懦懦地答应了。
开学了,我按照铁二哥的指导,内心忐忑、表面坦然地去他班老师那做了证明,说他交够了筐数;他也信守承诺,来到我班做了证明。没想到,两个老师都相信了,是不是我们平时的诚实起了作用呢,无从知晓,反正那天下午玩得踏踏实实,不亦乐乎。
开学典礼上,校长讲话,表扬了全体同学都完成了假期积肥任务。接着话锋一转,说道:虽然各班上报的数量都够了,可是学校的粪堆没长多少高度,没大多少宽度,说明这些数字有水分啊。当时,虽然对“水分”的具体含义不甚明了,但还是感觉到了校长的意思,我有点内疚,可又一想,大家不都在互相证明么?于是稍有安慰。中午放学,撒欢儿出校;下午一玩儿,一切都在九霄云外了。
多年之后,发小聚会,谈到这事,渐渐领悟到:生产队每天有多少牲畜出车,产生多少肥料是定数啊,要求我们上交的总量却远远高出实际的数量,不用谎言是绝对完不成指标的。令人疑惑的是,校长和老师不可以轻易计算出来么?
很快,又一个秋天到了。那天下午,我正在家里啃着一支烤玉米,小广播里传出一阵低沉得让人心抖的音乐,这已经是一年里第三次听到了,又一位伟人陨落了。全大队似乎瞬间慌乱起来,“四类分子”一下子被集中起来,几天几夜没让回家。几天之后,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追悼会,所有社员(村民)和学生聚集在学校操场上,民兵荷枪实弹把人群团团围住,枪上的三棱刺刀在阳光照射下闪着瘆人的白光。更可怕的是,我们这排站在最边上,紧挨着民兵。我旁边的民兵就是我家后院的丁老三,平时嘻嘻哈哈,今天格外严肃,直得像一个树桩子,弄得我都不敢多看他一眼。
临开会的时候,老师嘱咐我们,一会儿大人要是哭了,我们一定要跟着哭,声越大越好,但是开始有人讲话时候不要出声。于是开会前,我们几个拼命酝酿,猛想一些可以拿来哭的事情,但想着想着就打闹起来,怎么也找不到那个情绪,用现在的话说,我的泪点太高。
追悼会开始了,有人在致悼词,那口音我们也没听明白几句,就感觉空气格外沉闷。左边有大人在小声哭,偷眼一看,是我班女生翠红她妈——大队的妇女主任。我们按老师的教导使劲挤眼睛,可眼泪还是没有成功滴下来。悼词一结束,就听到人群里一片悲声,看到大人们那么伤心,我心里也有点儿难受,无奈何就是哭不出来。我家前院的王大婶哭得倒在地上打滚儿;胡三姑一下子背过气去,好几个人架着她,还有人在掐人中。我想起她俩在街上因为猪拱菜园的事对骂的场景,又忍不住想笑,但一扭脸看到旁边的刺刀,一下子憋了回去,使劲干嚎了几声,可眼泪还是没掉下来。
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回教室了。看到女生们脸上的眼泪和鼻涕,我和二愣子狗剩四锤子有点犯愁,因为我们都是哭点高笑点低的熊孩子,在那场合能忍住笑一半是老师的叮咛,一半是刺刀的震慑。但没完成哭的任务还是觉得挺没面子,更怕老师认为我们是“阶级敌人”。因为她说过,这个大会上,人民群众一定会特别悲痛,会悲痛欲绝;而阶级敌人才会暗中高兴,伺机捣乱。突然,四锤子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拉起我们几个就跑,来到操场一角的水井旁边,压出水来就往我们脸上抹,我们也心领神会,“伪装”之后战战兢兢回到教室。老师正在瞪着红红的眼睛挨个端详,看我们进来,也不说话,盯着我们几个“水脸”看了一会儿,没再言语。我们如释重负,回到座位,再也没敢抬头。
时间过得好快啊,眨眼间几十年过去了。“初老症”逼得自己经常回忆,有时一闭眼,还能看到那个沉甸甸的粪筐,还有那把闪着白光的刺刀。
【编者按】这是一篇生动有趣的叙事散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和梦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沧桑和回忆。那个年代的很多经历现在看来很荒谬,但那时候真是乐在其中,所以整代人身上那种身处逆境却从不悲戚的乐观主义精神,足以令后来者深深敬佩。我至今也记得小学时候到地里复收花生地瓜,拾麦穗搬玉米秸,去山里挖药材摘松果……那么多的任务我经常完不成,老师们检查时从来不过称,全靠目测估量,报出的斤数常常超乎我们的想象。大人们和孩子集体撒谎的行为顿时成为大家的趣谈。这么多年过去了,作者越来越喜欢回忆那些有趣的经历,那些谎言里蕴藏着多少暖人的情谊啊!希望看到作者更多的文字分享。推荐阅读。编辑:天海蓝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