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此青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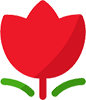 2
2

在平原荒芜,岁月冗长的家乡,我度过了非常美丽的童年。岁月流光,弹指而逝,每当面对朦胧的碎片记忆,依旧会怦然心动。
尽管时光在剥夺年轮青涩的梦想,不难想象暗夜里沉寂的一切正在悄悄绽开。赋予了它一种独特的万千气象。仿佛一个人经历沧桑后会变得深沉而温婉可亲。这种魅力,藏匿于那些落花流水,终去时,依旧能在岁月温情而又虚无的变迁中闪耀华彩,不动声色地传播其中难以泯灭的悲欢。
千般美丽中有一半是冰糖番薯,有一半竟与青草有关。期待盛景常驻,是来自人性深处的执念,那些与此乖违的人事境况,总难免让人惆怅感慨。我终有机会把那些镶刻在泥沙和荒野上那一抹青绿捂在胸口,紧紧簇拥在怀里。体味至情至乐的深远旷怡。
家乡的村庄径直向南去,蹚过几里蜿蜒曲折的沙土路,伟岸挺拔的大片槐树林屏障了广阔的田野。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升腾着时而飞,时而停,时而轻扬的情怀,一切都是周而复始,大自然用率真、担当的表情重现唯美生动而丰富的未来。林子四周荒沙缓缓聚拢围绕,为贴近大地的天籁之音留出了一席之地。仿佛一阵风的来去,仿佛阳光与风雨的交织来表达内心欢乐和气势,极为适宜。即便在晚上夜静时,稻麦香和虫鸣声便从这里阵阵传递,这种香气和声音至今仍能在耳边听见,闻到。置身旷野中,任凭流沙的轻易飞旋和风儿的肆意撕扯,我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天地的无垠阔大。这一切,定从那片荒沙布满的青草散布久远。并一直牢固地在我的梦境里生根茁壮至肥沃。
初夏刚过,大雨滂沱,天空如洗,水天一色的远方,洁白的槐花缀满枝头,装扮着慢慢游移的云朵,微风里飘飘而来时时弥漫着清淡甘甜的微香,总会下意识地眯着眼睛,嗅上几口,顿时觉得肺腑经受了美好的洗礼,不忍叹出。那种从容朴素的家乡味道浸润着黄昏的囱烟,我时常为能寻觅到儿时的欢悦而惊喜不已。凋谢的槐花铺盖在泥土上,新鲜干净净的颜色尚未褪去,偶有风儿拾起,花魂的银链便自由地向田垄两旁飞扑过去,到很远的地方微微颤动着落下去,逝去的花以自己的姿势装扮着逝去的美。实际上源于深刻的爱与不舍。观落花是件愉悦的事情,我和小伙伴们多次沿着河岸看落花飞,也和黛玉一样把花装在布袋子里,挖个土坑找个地方埋掉。树梢上的槐花抢着在初夏来时开得枝头第一枝。于是,便一群群一簇簇挤挤闯闯如狮子滚绣球,从四方奔溢而来,转眼盛夏如期,艳丽的色彩,飞翔穿梭的美妙姿态都在瞬间存在和消散中展开。林子里浓郁成荫就连阳光的锋芒都被宽厚的枝叶一并收纳,风声中似乎一切变得更加锐利,像成千上万只的翅膀扑棱棱过来,能飞的时候就飞一会,如果没有飞翔的伤痕,回忆的时刻都会黯然无光。就连荒沙地上,密密匝匝的野草如同实物被碾压成了一幅幅油画。此时,悲欢离合的故乡拢纳着这种蓬勃清新的气息,这种朝气如此美丽而高贵。它把我带进一种生机盎然,慷慨无邪的生活。
泥土里长大的孩子帮着家里过早干着农活,是分内的事。下午放学后操场上的蜻蜓像飞机一样低慢盘旋着。成群的孩子三两结伴,背着挎篓,装着镰刀欢呼着,像一只只大蜻蜓一样,兴高采烈地向槐树林飞快跑去。单纯的快乐从那敦实而热烈的欢呼中奔涌而来。那些快乐,短暂地粘贴着成长的缝隙。黄昏的临近,浓烈的汗腥味儿从歪歪扭扭的,钻出鞋子的“五个萝卜洞”里,冒着。挎篓用荆条编织上面有弯曲的木棍便背在肩上,用一条粗壮结实的绳子系在弯曲的木棍上,塞进草时咯吱咯吱地响。孩子们你追我赶像青蛙一样跳来跳去,在田野里寻找着肥硕的草丛。总有几个手脚麻利的,不一会儿绳子搭在挎篓的青草。脚用力撑着。走一路,掉一路,灰蒙蒙的天空下,熟悉的节奏准时在这个季节赶过来。只要雨一停,准能找到又肥又厚的青草地。从后面看不到人影,不用多问,一准知道是三叔家的小蛋,这个调皮捣蛋的小子,犟着呢,手被绳子勒得通红也不哭,镰刀昨晚上在家中已经磨得银光锃亮,拿手轻轻一试,不小心就能碰出血,吹根头发,当即拦腰斩断。只要看到肥厚的青草,一把薅住,紧握着拳头,贴着地皮,镰刀飞过,不多会儿便有沾着泥沙的青草齐刷刷地躺平在身后,镰刀发出破碎的声响,撕啃着大地生长的愉悦和生存的骄盛。偶尔也会有一大片积雨云在这里集合,跟着雷声轰隆隆的鸣响扇面般铺展开,雨点顿时像千军万马奔腾过来,碰巧时,雨直杵杵的就在地沿东边空降。顷刻间晚霞满天,握镰刀的小手胀痛发麻。装草喽!装草喽!这时的,延绵其中的欢乐微乎其微,泥路上,结伴而行的割草队伍缓慢前进着,其中,有我的两个哥哥。大哥十二岁,二哥九岁。
此时露台外面的小雨不知来于何时,从树叶,房檐和不知名的地方跑过来,毛绒绒的绿色再次吸引我的视线,帘外的草坪茂盛如新。我只觉得那些草仿佛要对我说些什么,我静静地伫立,似乎听得懂草的情愫,空气中的风和细雨的喃喃絮语。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哥哥在乡下老家生活。母亲是县师范学院毕业的语文老师。在村子里教语文和音乐,建国前参加地下抗日工作,家境自然要比邻居们宽裕许多。品貌出众且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是外祖父的独生女儿,外祖父诗书传家,待人厚德,把幼年母亲送到距家三百里路的县城读高小、师范。母亲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能双手打得算盘。乡亲们敬重母亲字写得清秀整洁,宛如母亲绣在领口的一朵荷花。邻村有的步行几里路,用一篮鸡蛋,一提挂面,来托母亲给在外面当兵的儿子写封家信。不识字的人敬重文字,信赖母亲的为人,母亲总是轻声细语地问着,家里的详情,一边铺开纸,听她们絮絮叨叨说着家长里短,诉说思念之意,告知一些家里的近况和对亲人的牵念,有时也会微笑着在信中替他们表达心切之意!想必我日后在写作上小有见术,过早地被艺术的光束笼罩,与当年看母亲经常写信密不可分。家中的零活都是母亲亲手教哥哥们一样一样去做。出于安全,母亲亲自挑着水桶领着哥哥到村南学挑水,大哥个子高,做事乖巧,一边看母亲把井绳扔进井里,连续摇晃着,两个哥哥忙着摇动辘轳从井里把水桶搅上来。桶里水刚过一半,再用另外一个桶扔到井里,重复几次后,两个水桶都满了大哥颤颤悠悠地挑着水桶往回走,二哥在家帮着往水罐里倒满。记忆里的母亲一边熟练地在学校教书,教叔叔和姑姑们写字,唱歌,回家来教哥哥们学做家务,打扫庭院,从不让哥哥和别的孩子在麦秸垛上疯玩。有一天,两个哥哥噘着嘴,私下里委屈地小声埋嗔着母亲的严厉,并悄悄幻想着美好的未来:去打玻璃弹球,自制印模。母亲看出了他俩的心事,大多时在一旁偷偷看着这两个随时向命运发起挑战的儿子。暗自期待着他俩的胜利。物资匮乏的年代番薯是家常便饭,母亲怕我们吃腻,总会变着法子做出美好的味道,至今想起,仍觉得美味儿在唇齿游来游去。让我怀念不已。两个哥哥从小听母亲的话,都在努力尽一己之力帮着母亲创造着微薄的财富。二哥虽小,但心智早熟。总是等一家人睡了之后,再去紧盯着大门是否上栓,关紧窗户,以单薄的身体和弱小的能力呼应着母亲的爱,母亲作为奖励,必亲自做一碗香甜的冰糖番薯,难以言说喜悦和爱意都写在脸上。母亲格外谨慎地脱下教书时穿的那件黑色丝绒裹着月白色包边的上衣,到里间屋换上姑姑缝的蓝色带白木槿花的旧夹袄,顺手将围裙系在腰间。这个时候,我的世界里满是那透着亮光的甜水在眼前晃来晃去,小心拽着母亲的衣襟跟在母亲身后寸步不离,怕那淳美香溢的味道掉在地上,被那小鸟衔在嘴里我抢不回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哥哥在乡下老家生活。母亲是县师范学院毕业的语文老师。在村子里教语文和音乐,建国前参加地下抗日工作,家境自然要比邻居们宽裕许多。品貌出众且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是外祖父的独生女儿,外祖父诗书传家,待人厚德,把幼年母亲送到距家三百里路的县城读高小、师范。母亲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能双手打得算盘。乡亲们敬重母亲字写得清秀整洁,宛如母亲绣在领口的一朵荷花。邻村有的步行几里路,用一篮鸡蛋,一提挂面,来托母亲给在外面当兵的儿子写封家信。不识字的人敬重文字,信赖母亲的为人,母亲总是轻声细语地问着,家里的详情,一边铺开纸,听她们絮絮叨叨说着家长里短,诉说思念之意,告知一些家里的近况和对亲人的牵念,有时也会微笑着在信中替他们表达心切之意!想必我日后在写作上小有见术,过早地被艺术的光束笼罩,与当年看母亲经常写信密不可分。家中的零活都是母亲亲手教哥哥们一样一样去做。出于安全,母亲亲自挑着水桶领着哥哥到村南学挑水,大哥个子高,做事乖巧,一边看母亲把井绳扔进井里,连续摇晃着,两个哥哥忙着摇动辘轳从井里把水桶搅上来。桶里水刚过一半,再用另外一个桶扔到井里,重复几次后,两个水桶都满了大哥颤颤悠悠地挑着水桶往回走,二哥在家帮着往水罐里倒满。记忆里的母亲一边熟练地在学校教书,教叔叔和姑姑们写字,唱歌,回家来教哥哥们学做家务,打扫庭院,从不让哥哥和别的孩子在麦秸垛上疯玩。有一天,两个哥哥噘着嘴,私下里委屈地小声埋嗔着母亲的严厉,并悄悄幻想着美好的未来:去打玻璃弹球,自制印模。母亲看出了他俩的心事,大多时在一旁偷偷看着这两个随时向命运发起挑战的儿子。暗自期待着他俩的胜利。物资匮乏的年代番薯是家常便饭,母亲怕我们吃腻,总会变着法子做出美好的味道,至今想起,仍觉得美味儿在唇齿游来游去。让我怀念不已。两个哥哥从小听母亲的话,都在努力尽一己之力帮着母亲创造着微薄的财富。二哥虽小,但心智早熟。总是等一家人睡了之后,再去紧盯着大门是否上栓,关紧窗户,以单薄的身体和弱小的能力呼应着母亲的爱,母亲作为奖励,必亲自做一碗香甜的冰糖番薯,难以言说喜悦和爱意都写在脸上。母亲格外谨慎地脱下教书时穿的那件黑色丝绒裹着月白色包边的上衣,到里间屋换上姑姑缝的蓝色带白木槿花的旧夹袄,顺手将围裙系在腰间。这个时候,我的世界里满是那透着亮光的甜水在眼前晃来晃去,小心拽着母亲的衣襟跟在母亲身后寸步不离,怕那淳美香溢的味道掉在地上,被那小鸟衔在嘴里我抢不回来。
母亲用清水将红薯清洗两遍晾干,切成四方块,放在锅里炖上半个时辰,这时,大哥忙着往灶里添柴禾,二哥往锅里倒水,火焰跳动着欢乐的舞步,母亲用铲子捅捅红薯又软又烂,就从抽屉下面储物箱的小木匣子里摸起几块透明的冰糖,小心翼翼地放到锅里熬,有时再撒上几粒白芝麻一块炖,这时候的太阳慵懒地不肯挪动半点脚步,等啊等,掀开锅盖,冰糖芝麻和红薯正在缓缓融合在一起,泛着几近透明的金黄的软泡泡,小小的芝麻像极了摇头摆尾的小鱼儿,在夕阳里泛着金波的河水中荡漾。母亲用木铲子顺时针慢慢地搅动着粘稠的汁,越来越松软,越来越粘稠香甜松软可口的冰糖红薯就做好了。于是,哥哥们一回家就忙着写作业,帮母亲做家务,期待着灶台上一碗香甜可口糖水。我的母亲终于没有辜负我和哥哥们的期盼,六只小眼睛和垂涎欲滴的嘴巴终于等到了。于是,厨房里香甜阵阵,小院里阵阵香甜,母亲总会留给我一小份,二哥经常会把碗里剩下的甜水,用手指头抹在我的嘴里。母亲走后的许多年间,心里始终燃烧着那天下午永不熄灭的慷慨的焰火,每想到就会感觉到一股隐秘的痛楚从生命经历看不到的低洼沟坎中淌过。梦想里柔和的糖水在生活中微微甜着。这时大哥会蹲下来背起我满院子转着圈子跑,我们兄妹三人像春天的小燕子飞来飞去,我强迫自己用心聆听过鸟的震颤,它们的鸣啭和啼叫,远不及院子里追逐旋转缠绕在一起悦耳。这声音在苍凉且泛着涟漪的寒冷的季节,让身体有了片片暖意。因着母亲的爱,成长环境的艰难困苦都化成甜美,化作在那微不足道的食物里。每一幅画面,每一个细节,都是对自由旷达生命的诠释。在惯常的富贵荣华,功名利禄的人生奔逐之外,还有一种另外放置生命的方式。并从中获得心灵的愉悦和性灵的飞翔。于昨天与明日,让我们活得简单,干净温暖!
在疫情袭来的夜半台灯下,我时常想到,如果幼年时没有母亲给我们兄妹三人做过的冰糖番薯,如果没有那种味觉最简单的满足在年久月深里浸润,那么整个人生终将会失去了透明融合的颜色。我们又能拿什么来抵御岁月无情的磨砺呢?母亲性情坚强,宽容大方,聪慧睿智,我也是在而立之年才领会到了这种豁达温和的为人处事方式,自然,这都是母亲遗传基因的足够强大,让我不能轻易地发怒怨恨和计较生活的枝节,而乐意从容坦然接受一切,处变不惊,需要坚强的毅力和临危不惧的决心。同时也让我获得对人生的满足和慰藉。数十年间,这些情怀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主旋律,重新发现时,原是母亲早早就此埋下伏笔。当然也是母亲丰满人格的生动延展。 那年秋天,秋雨连绵过后简直就是一场青草肥硕大爆炸,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大自然和谐平静瞬时被打破,田野的青草葱绿云集蓬勃辽阔,奋不顾身或亲切或陌生,让人一看就情不自禁惊叹的绿,从大地边缘滚动蔓延,汹涌而来仿佛从未被尘埃眷恋,没有呐喊,没有纷争,看夕照下安适的河底,那是清泉穿岩,那是流云行岙。劈头盖脸猝不及防的奔涌般与世界撞个满怀。
那年秋天,秋雨连绵过后简直就是一场青草肥硕大爆炸,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大自然和谐平静瞬时被打破,田野的青草葱绿云集蓬勃辽阔,奋不顾身或亲切或陌生,让人一看就情不自禁惊叹的绿,从大地边缘滚动蔓延,汹涌而来仿佛从未被尘埃眷恋,没有呐喊,没有纷争,看夕照下安适的河底,那是清泉穿岩,那是流云行岙。劈头盖脸猝不及防的奔涌般与世界撞个满怀。
秋假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叫醒刚刚准备休眠状态的两个哥哥并肩站在院里大梧桐树下。满眼的翠墨奔赴初秋的阳光里,小院静谧安详。几只花斑鸠在树上咕咕叫着,仿佛在唱着自己的歌谣。哥哥们互相挤挤眼睛,不知母亲要给他俩说些什么。母亲拉着两个哥哥的手,给哥哥们布置了假期割草的任务:割一千斤草,不是湿草,而是晒干后的草。哥哥们面面相觑脑袋在脖子上转来转去,不知道一千斤干草意味着什么,只是感觉倒是母亲通过指定的数量,督促干活。母亲目光温和且坚定地说道:割草是这个季节是最适合的家务活,既能帮衬家里微薄的收益,减轻经济上的重负,又能帮助身体上的成长。阳光斜照在母亲明媚的双眸和那双拿粉笔和浆洗衣服的白皙的手指上。母亲抚摸着两个哥哥的肩膀,以及绵延其中的疼爱和悲欢。两个哥哥并排站立在母亲面前伫立良久,听说能为家里带来经济上的收入,大哥嘴角翕动了一下,二哥仰起脸望着大哥,终于两人互相交换了眼神,在母亲再次鼓励和肯定下,坚定地答应了。
这次割草行动为我们的童年时代披上了坚强的勇敢色彩。也使我们兄妹在日后有了战胜恐惧和绝望的法宝。
母亲不动声色地早有准备,是那种做事果断干练的人,已经找邻居木保大爷做好了一辆独轮车,置办了新装备:买了新篓子,新镰刀,军绿色水壶,新毛巾,和两双解放鞋。晚饭后,皓月当空,秋风微凉,打麦场空无一人,母亲带着哥哥到村边的麦场上练习推车,起初,哥哥推着拐弯就翻车,几次连人带车一块翻倒在地,练了几个晚上已经熟练掌握了独轮车的这些技巧,母亲说:有了独轮车,再不用挎篓背草,你们兄弟二人相互照应着,会事半功倍。我知道,我们的性格里都有母亲坚韧的一面,我们终将长大,终将离开母亲的庇护,羽翼渐丰,大哥是车双辕,二哥是前后轮,年幼的哥哥们付出艰苦卓绝的劳动影响了一生的命运。
晨光熹微,蒙蒙发亮,大哥娴熟地推着独轮车奔走在前面,车上绑着篓子,镰刀,车把上搭着毛巾,二哥斜背着绿色水壶雄赳赳紧跟其后,大约半小时,秋草葳蕤的槐树林迎面扑来。安置好家俱,哥哥们驻足四望,绿野满坡,刺目的阳光从槐树林里枝叶间飞泻直下,被插入泥沙和厚草的地面。苏醒的时刻到了,深绿和褐色的草深深扎根于沙土地,时而簇拥紧抱,时而匍匐地面,草地的沉睡者并不知道来了一场大迁移,反倒是命令仪式。树林里密不透风,凉爽舒适,熟睡的露珠被细碎的脚步惊醒,如入无人之境,荒地上热浪沸腾如芒刺在背,裹挟着泥沙和圪针的青草攥在手里,稚嫩的皮肤先是被晒得通红,几天下来,后背起白皮,手上磨出了血泡,圪针在胳膊和腿上密密麻麻的激烈刺痛,后背变得黢黑黢黑。起初连续割草,强大力量的摧毁之下,身体变得四分五裂,浑身酸痛,回到家顾不上吃饭倒头就睡着了。第二天清晨,哥哥们从未表现出丝毫的犹豫和退缩,母亲看到了哥哥骨子里的坚韧,早早把水壶装满,哥哥们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再次被母亲深情托举,毛巾和鞋放在窗外,用超凡的意志力和疼爱轻声叫醒。此刻窗外,稻田绵延,稻香起伏,自有劳作着埋首其中,风吹草动绝不能让他们低头,母亲的话语里刻满了鼓勇和爱怜。只因为那种推动,刹那间给予了勇气和征服的力量。在多年后的今天,我有幸拜读到一行禅师《正念的奇迹》时,瞬间泪如雨下,母亲一定没有机会读到过这本书,却能用更为澄澈无碍的眼界使得绝望与希望产生微小却关键的差别。这种强烈信念的本身就让我感到震惊,让我们时刻在日常生活中都保持正念和清醒的母亲,让我学会把一部分时间留给自己,可以读书,跑步,写文章,安住其中。我很难形容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柔韧,湿润,音调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转折,我试图寻找这种封存时间的力量。母亲,并没有给我明确的信息,让我的视线总不自觉地引向远方。
四野空旷,秋雨洗净整个平原,伴随而来的野花恣肆开放,秋草吹又生。整个假期,哥哥们穿梭在田野深处,传递着心灵的默契。大哥轻巧地推着独轮车,秋风从绿野间吹拂而来。那些封存于时光深处的气息韵味,用一种鲜明的图案呈现了它的存在。晚归的路上满车青草高过大哥的身影,二哥在前面肩膀用一根绳子用力拉着,一推一拉,从不迟疑与停滞间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把多少个黎明和黄昏都与青绿一起收获。大哥比二哥大三岁,结实的臂膀和高挑的个头比二哥高出一大截,干的活儿自然多些,母亲身材高挑的优秀基因,我们兄妹三个勇敢地接受了母亲坚强的毅力,并毫无保留地传承下去,大哥性情豪爽,晒得黢黑又瘦,如果脖子里戴一个银光闪闪的项圈,真的就是少年闰土。只要看见二哥停下手里的镰刀,就知道是累了或者是饿了,慌忙从上衣的口里的小袋里摸出一小块冰糖递过去,二哥忽然咧咧嘴露出洁白的牙齿,羞涩地笑着,小心放在嘴里。哥哥们仍然有条不紊满怀母亲希望的梦想。不厌其烦重复着眼前的事。槐树林里,树高草茂,大哥看好地形,兢兢业业尽着一个淳朴兄长的本分。多年之后,我们兄妹三人仍能在一起相互搀扶着抵御岁月的萧瑟和长夜的严酷。大哥宽阔的后背仍能让我躲避寒冷和无常生活。每逢清明节,大哥总是一大早赶到乡下老家煮上父母当年爱吃的茶,站在村口熟识的老槐树下远远等着我的到来,还习惯把落槐花堆在一起深深掩埋,他脸上常常带着母亲留下的笑意,我甘愿冒着寒风吹透棉袄,搓揉着耳朵,一路小跑,奔向那在夕阳或晨曦中的小院。它知道我们的幸福感并非来自物质的多寡,归属和宿命的诞生都在那乡下简朴的院落里。但觉根系笃实,内心熨帖。
母亲征得在大队当支书的三大爷同意,在村外闲置的打麦场临时找了块地方。趁着夜里风高,月朗星稀,我勤劳淳善的母亲带着两个哥哥平整麦场,母亲用铁锹把砖瓦、土块都铲成一小堆,两个哥哥用手推车推到远处的土坑里,母亲教书时朗朗上口,歌声飘到村外的槐树林,周身散发着美的光芒,做起农活来专注而热情。庆幸的是,母亲倾尽全力馈赠于我真传秘籍,我竟不迟豫地接受了母亲的性情,天然觉得有义务接下家中未竟的种种人情世故,在三十八岁时,我用同样专注和热情的双手缓慢而又坚决拢合母亲美丽的眼睛。用母亲沉着而又坚定的呼吸,带领我和哥哥所有儿女们用冷峻的目光凝视前方,永不停歇,全然不顾生活应该怎样对待,无视前方荆棘满途,依然轻描淡写地还原儿时的快乐。

每次割草回来,都要把草平摊在打麦场,等待着风吹之后,太阳再晒过。夜里刮大风或有雨,母亲还要跑过来用雨布遮苫住,晒干后的草干瘪瘪趴塌着薄薄的一层,不小心就被风吹跑了,二哥望望邻家厚实的草垛,偷偷地在墙角抹眼泪。一个月的时光很快过去了,垂柳瑟瑟的抖动着渐渐泛黄的树叶,田野里的麻雀熟识地在哥哥车把上不停地蹦来蹦去,眼看着一层层晒干后的青草,像涌动的山峰一样慢慢升起来,哥哥们兴奋地欢呼,像两只小狮子高兴的在草垛上翻滚。母亲抚摸着大哥晒得黢黑的脊背,二哥红肿发紫的肩头,默默地在一旁翻着草垛,我已经是一个十五岁孩子的母亲,全然知道了母亲当时的隐忍和顽强,给予儿女们孱弱的力量和尊严,让孩子们被光明和欢乐照拂,母亲一定背着我们流了许多眼泪,甚至走在漫长而又艰苦的光阴里泣不成声。母亲像战场上的将军,哥哥们就是不屈不挠的小勇士。母亲那晚做的糖水番薯满足和快乐的味道,多年以来,日夜流出激越的乐曲之泉。最终,自家晒干后的草垛在打麦场上高过邻家,稍有空闲,母亲总是一个人去晒场上翻草,等待着在清晓或夕阳中晚归的哥哥们,出现在明净的视野。兄妹三人一齐在月色如洗的小院里,随心所欲倾听母亲亲自缔造的神话,把贫乏的花布碎片,给我拼接成鲜艳的长裙。我之于母亲的爱是自由而美好的,母亲贡献的爱,热情和力量,我全然懂。相信河流酝酿荣枯的热情消失殆尽,而山峰每年都长出清脆的岩石。尘土杂草间,哥哥的独轮车碾轧出了自己未露的心迹,小径远去,寻常的脚步被时间记忆在了生命最珍贵的年岁。我从来没有想到山峰会崩塌,巨浪会席卷了老家高大的院墙,没有想到母亲会在我的而立之年,连同美妙的音乐一道沉入无限的静寂。我只带着母亲的琴,一支笔。黄昏将临,山路断绝,在我坚守不住最紧要的隘口,母亲以磅礴的气势为我壮胆,伸手一把拽在怀里递了一碗滚烫烫的甜水。瞬间慧眼阔开,力气无穷!
那哭声和泪水里定有我们兄妹所不能知道的忧心如焚,有家庭繁琐纷扰工作上的辛劳和纷争。母亲精明聪慧的意志和性格,决定了她一边把微薄的薪水补贴家用,一边让心爱的小儿子们用肩头扛起生活的苦楚,我不能想象母亲当年从县城中心学校调到贫困的乡下,在苦难的生活面前佯作镇定,究竟需要多少勇气和坚定抉择,母亲离外婆家五百多里,山重水复,常年不能回去,在宠爱的外祖父面前弹奏舒心的曲子,谁又能给予母亲一个温暖的依靠。想到这里我早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只感觉欲心碎,欲断肠,为母亲,为我不曾谋面的早逝的外婆。
一路鸟鸣蝉语,已经有不少泛黄的树叶,轻轻地落在路边。
看哪,池水深且满,像麻雀的眼睛一般迷离,午后的风穿梭在树林里,诉说着隐藏在绿荫中的秘密,七〇年代初期,春风浩荡开拓着大地划时代意义,我们有幸陪伴在母亲身边,目睹着,感悟着生命之于她的艰辛和磨难。母亲隐忍着生活给予的虚幻的罗网和欺骗!然而,母亲从来没有表达过生活的埋嗔以及对外祖母的眷恋哀思。因为,母亲有音乐,这欺骗可以付之一笑并且淡忘,当然,有我们三个甜蜜而又惊奇的双眸顾盼时单纯的存在,日复一日,步履疲沓的黄昏尘土飞扬,几番鸟鸣蝉语,迷失在苍茫黄昏里蹒跚的树叶已在和昨日昔别。
假如就这样,鸟儿倦了,风也吹不动,两个哥哥期待中的欢乐一样在仁慈的阳光下苏醒。没有一丝轻云的遮盖,没有一丝远雨和着秋风里席卷着的黄叶起伏摇曳,田野里顿时欢腾起来,忽然间一只蚂蚱从草叶上跳了出来,两个哥哥你追我赶,继而便猛扑了过去,想捉住它,偏又捉不住两个人用毛巾互相追赶,捂住了,一松手又不知跳到哪里去了,不由得跟着它在田野里撒欢儿嬉戏,阵阵地荡起共鸣的回音,旋即又刮起惊扰的狂风,等待着一丝不期而来的急雨,如释重负地卸去汗珠,大哥用柳条编了密实的草帽,戴在两个人头上,乍看上去像小兵张嘎潜伏在草地里。又遮阳又调皮。昨夜雨疏风骤,露珠在草叶上颤抖翻滚,槐树叶子在头顶沙沙作响,空气清新,霞光满天,树荫里知了的歌声已失去了往日的嘹亮,含泪而暗淡。依稀能辨认出乡下旧日村庄模糊的轮廓,时而呈现清新嫩草的绿色,时而呈现冬天谷禾的饱满。
如今,我以一成不变的面目把自己献给曾经爱着的色彩和无限激情那是不够的,但它却回响在我的心里,而我的双眸寂然无声。夜色正因此而颤栗。
良久之后,它们让我感到言语的黯然失色和一切的虚无,它们就是短暂的聚散,繁星宛若一滴滴炙热的泪珠闪烁在无知的黑暗。我站在这里,望着横亘在眼前雄浑的太行山脉。世界何其之大,人事何其渺茫,好像一切刚刚来过,又才刚刚离开。 装满草的手推车,看不见路,怕母亲担心回返的路上推车会翻到路沟里,或者是被镰刀割破了脚指头,哥哥们快走到村口时,吹柳叶哨,吹草叶哨,苇叶宽了,吹苇叶哨,哨声有时像燕子,象叫天子,或者什么也不像,反正吹的都是少年心事,我常听见哨声悠扬地划过黄昏,在这寂寞而又趣味无限的乡村上空灵巧地翻越。故意高声说笑着,引着母亲的视线发现他俩的独轮车上高高的青草垛,推车,拉绳,披星戴月。母亲总能在晚归的割草队伍认领出自家孩子的水壶和被泥沙打磨后的解放鞋,晾晒后的草垛终于成拱山崛起。是母亲掩藏了多少未知的隐情和秘密,我感知到她的眼泪已经从容学会了微笑的语言,一直鼓励推动着两个哥哥付出艰苦卓绝的劳动。以及对我们心灵的宽慰和护佑。在奔波的路途中,我愿意停靠在岸边,冲破云层,用带着永恒节奏的言语向母亲娓娓道来。
装满草的手推车,看不见路,怕母亲担心回返的路上推车会翻到路沟里,或者是被镰刀割破了脚指头,哥哥们快走到村口时,吹柳叶哨,吹草叶哨,苇叶宽了,吹苇叶哨,哨声有时像燕子,象叫天子,或者什么也不像,反正吹的都是少年心事,我常听见哨声悠扬地划过黄昏,在这寂寞而又趣味无限的乡村上空灵巧地翻越。故意高声说笑着,引着母亲的视线发现他俩的独轮车上高高的青草垛,推车,拉绳,披星戴月。母亲总能在晚归的割草队伍认领出自家孩子的水壶和被泥沙打磨后的解放鞋,晾晒后的草垛终于成拱山崛起。是母亲掩藏了多少未知的隐情和秘密,我感知到她的眼泪已经从容学会了微笑的语言,一直鼓励推动着两个哥哥付出艰苦卓绝的劳动。以及对我们心灵的宽慰和护佑。在奔波的路途中,我愿意停靠在岸边,冲破云层,用带着永恒节奏的言语向母亲娓娓道来。
我清楚地记着,早饭收拾停当后,母亲在家换上那件黑色丝绒上衣,扎上白色的纱巾。到大队部与外村来的生意人商定之后,把买草人领到自家的草垛前,翻看成色,熟练着拨打着算盘和来者讨商定价,母亲豁达爽朗的性格总能让外人满意,很快,七八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儿把草垛用两个大车装走了。母亲奖励给哥哥每人一元钱。顷刻间,沸腾的脚步和群鸟欢呼声在狂奔供销社的路上尘土飞扬。水壶、毛巾、军鞋已经七倒八歪地抛撒在炊烟升起的昏黄的天空之中。
多年之后,我和两个哥哥仍旧保持着乡下孩子的淳朴的本性。相信自己,越是相信,它就越是坚硬和任性,母亲必将以清风明月之轻盈,变得虚无而又真实。家乡那一缕无声流淌的绿早惊扰了所有静止不动的内心世界。我的血液里流淌母亲的血液,格局和坚强的毅力。我是母亲的影子,是母亲留在这个世界上音符跳动的最强音。常能面对复杂的人情世故懂得取舍,永不失向上的信念。我深信,必定是母亲深埋在生命深处治愈心灵重创的秘方。
一时间,眼前恍惚浮现当年的胜景,鲜明而清晰,就像此刻旁边那棵槐花树,一阵微风吹过碧绿的青草,蓦地过来一阵浓郁的冰糖番薯的芳香。
【编者按】作者通过糖水番薯,割秋草等生活场景,细细密密地从多个角度,塑造了一个“最美乡材教师”,我的母亲。人间第一情,灯下小儿女,童年的味道,少年的艰辛,都深深地浓缩在了作者的文字中。推荐阅读。编辑:穿越中的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