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地理】促织奏鸣曲
 点击:2591 发表:2024-03-12 12:59:27
点击:2591 发表:2024-03-12 12:59: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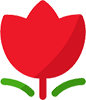 10
10

第一乐章:风露渐凄紧,家家促织声
对我来说,秋天是从夜晚听到的第一声虫鸣开始的。
唐代元稹在《处暑七月中》写道:“向来鹰祭鸟,渐觉白藏深。叶下空惊吹,天高不见心。气收禾黍熟,风静草虫吟……”处暑之后,秋意渐浓,庄稼成熟,秋阳煦暖,秋风安静,天高云淡,草虫吟鸣,好一派岁月静好、天地安宁的模样。
促织的叫声清亮悠远、张弛有度,不急不缓、不聒不噪。老家的方言中没有翘舌音,又多儿化音,所以把促织叫做“促(读上声)鸡儿”,这个称呼通俗自然,没有丝毫浪漫气息,却亲切,甚至可爱。
立秋后促织开始展示自己的魅力,天一黑,草丛里就传来“瞿瞿嘘嘘……” “唧唧唧唧……”唱得清澈嘹亮,霸气十足。
母亲说,“促鸡儿”是在催我们浆洗被褥呢!我不懂:“不过就是些小虫子叫,难道你能听懂它们在说什么?”母亲说:“你听,它们说的是‘浆浆捶捶’ ‘浆浆捶捶’……”
我于是每天晚上都认真地聆听它们的鸣叫,“浆浆捶捶” 、“浆浆捶捶”……这节奏明快、音色美妙的虫鸣一起,秋天的况味就意境悠远了。

母亲和邻居大妈大婶们开始翻箱倒柜,把家里的棉衣、被褥全都找出来,一件件拆了,把棉花晾晒在向阳的地方,棉布的表里、床单枕套拿去河里捶捶打打洗干净,再刷上凉透的自制米浆,挂到铁丝上晾晒。
吸足了阳光的棉花被母亲用棍子用力拍打,变得松软透气,浆洗过的棉布挺括结实、干爽硬朗。母亲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铺上凉席开始缝制棉衣、被子,我帮她抻被角、认针,把脸贴到被子上,扑面而来的满是阳光和粮食的清香。
原来促织的名字竟有如此深刻的含义,“札札草间鸣,促促机上声。”“促人机杼意殊深,彻夜啾啾不绝吟。”促织鸣而天下知秋,催促人们不要懒惰,早备寒衣以免受冻。母亲们不用织布,也要赶在秋忙前浆洗被褥、缝制棉衣。
促织当之无愧是秋天的使者。
第二乐章: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
老家地势平坦,农田肥沃,是县里的农作物种植大镇,小麦主打,套种玉米、间种大豆,岭上坡地种花生、地瓜。春夏秋冬循环往复,地里的活儿紧锣密鼓一样儿也不能马虎。

仲秋时节,早出晚归的大人身后,必定有一两个蓬头稚子作跟屁虫。母亲眼里没有闲人,她总能指挥得我团团转,转来转去就忘了主题,就去找小伙伴们一起捉害虫。乡村的昆虫五花八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大蚂蚱和豆虫备受青睐。
雌蚂蚱的籽金灿灿的,烧熟了以后油亮金黄,吃一口足以让肚子里没油水的农村孩子抵达幸福的天堂。体型硕大的油蚂蚱肚子里能塞下七八个花生米,烧熟了吃进嘴里从头香到脚后跟,至今想起来回味无穷。
黄豆收割之后去地里挖豆虫,一个小洞底下就有一个绿色的大豆虫在蠕动。回家洗净泥土,就着灶火烧成焦黄,吃起来香气四溢。豆虫和蚕蛹一样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却不需要花钱买,农村孩子如何不爱!
“促鸡儿”不能吃,不太受孩子们待见,就常常捉来玩消磨时光。小学课本中有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的观察日记——《蟋蟀的住宅》,主人公蟋蟀是一位思维缜密、行动敏捷、会弹琴唱歌的音乐家,很多同学竟然都没想到那只洋气的昆虫竟是农家孩子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促鸡儿”!
我却因它的报秋与催织而格外喜欢它。

夜晚,高高挂起的汽灯下,白天掰下的玉米在场院中间横亘成一道长长的山岭。女人们围岭而坐,麻利地剥掉玉米皮,每穗玉米底部只留两片玉米叶子。男人们用搓好的玉米绳,揪住留好的两片叶子每十穗绑成一提,再搬到场院边堆成玉米垛。小孩子也不闲着,在大人的吩咐指点下干得欢,但一会儿工夫就没了耐性,于是扎推去一边玩儿。
场院四周的促织振翅高歌。我们打着手电,蹑手蹑脚到草丛里寻找歌声的源头。那时候并不知道这悦耳的声音是翅膀摩擦振动发出的,更不懂得不同音调与节奏所蕴含的美妙深意,只晓得这天籁一样的虫鸣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赠,它让秋天的夜晚不荒凉、不寂寥,它让农村的孩子心里不空虚、不冷漠。
第三乐章:一声能遣一人愁,终夕声声晓未休
地瓜收获之后,一条条紫红或白色的长龙静卧在黄色的大地上,真让人无比欢喜。
红薯甘甜软糯,产量却低,充分晾晒吸足阳光拉回家窖藏,那是全家人过冬的口粮。白薯口感清淡,产量极高,为了方便储存,必须切片晒干,一部分用来酿酒,一部分留作过冬的食物。那些年,栖霞白酒厂酿造的“白洋河酒”在烟台地区久负盛名,白洋河自西向东流经整个栖霞的土地,是栖霞人民当之无愧的母亲河。白洋河的水酿造的地瓜烧、老白干,是上了年岁的农民辛苦劳作一天后用来解乏的口粮酒。

擦地瓜的工具是特制的,一块比搓衣板大一点的木板中间,镶着金属做成的刀片。母亲坐在地瓜旁,脚边放一个大号的箩筐,擦板宽的一头放进箩筐里,窄的那头搁置在怀里,左手拣地瓜,右手擦擦擦,配合默契,省时省力。箩筐擦满了,母亲起身活动一下酸痛的腰身,双手用力抓住筐子往空地上一扬,满筐地瓜片在她四周飞散开来撒到地面。我觉得那是母亲最美的时刻,简直就是仙女散花一样美丽动人。
我在母亲散花的地方蹲下来,把满地凌乱的地瓜片尽可能摆放整齐,便于晾晒。随着时间消逝,地瓜长龙渐短,地瓜片像雪花一样盛开在收获后高低不平的土地上。天黑了,促鸡儿的歌唱声铺天盖地,在寂静幽暗的田野中此起彼伏、浩浩荡荡。月光下,母亲背对着我的身影那么孤独,那么执着,那么倔强。
我又累又饿、又冷又怕。母亲停下来,塞给我一块干净的地瓜,又把她的夹袄披在我身上,小声说:“再抗一会儿,我把这垄地瓜擦完就回家。”我披上母亲的夹袄躺在她身旁,被太阳晒了一天的土地余温尚存,闭上眼,黑暗和虫鸣立即包围了我……
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家里热乎乎的火炕上。
第四乐章:悠悠清夜眠,促织催朝光

《诗经・豳风・七月》中有这样的描写:“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可不是吗,进入深秋,天气越来越冷,这些小脑袋大肚子、后腿发达且自带两排锯齿的小东西就毫不客气地跳进堂屋,在炕洞里和锅灶旁堂而皇之地过冬,仿佛天生就是我们家的成员。父亲烧火的时候看到它们出来蹦跶,怕灶膛里掉出来的火星烧着它们,总会像对待淘气的孩子那样把它们往旁边扒拉两下。有一年冬天,风匣子(风箱)的拉杆沉得很,我拉不动,还以为自己小胳膊没劲儿。父亲拆开风匣子,原来是挡板周边的鸡毛上藏满了促织,这些小家伙在风匣里安家落户,高枕无忧准备过冬了呢!
我们睡觉的火炕下面,在盖房子的时候就提前挖好一个炕洞,留一个只能容一个人进出的洞口,主要用来储存地瓜、生姜等怕冻的蔬菜,所以也叫地瓜窖。我是家里的老小,出入狭窄的炕洞非我莫属,小小年纪就能把一篓篓地瓜秩序井然地摆放整齐。冬天每次进窖取地瓜,烛光中的小小空间格外温暖,“促鸡儿”把这里当成了天堂,我常常与它们玩耍而忘了时间,任凭家人在外头长呼短唤都不答应。
我会专心致志地看它们健硕的大长腿有力地跳跃,往泥草抹平的洞壁上蹦,往角落里蹦,往地瓜堆上蹦。有时候会看到两只好斗的家伙打架,进退之间互不相让。有时看不到新奇光景,我就捉住一两只促织用手捏住它们的后腿,看它们一蹬一蹬地挣扎。

夜里,我在促织的奏鸣中进入梦乡,它们兀自在火炕下面的窖子里弹奏,在灶台边唱戏,让我倍增安全感。那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父母未老,我年纪尚小,家境清而不苦,贫却不寒,梦里不是化作大鸟在山林里飞翔,就是和小伙伴们在田野上奔跑,妥妥地感受到自己的成长。
尾声:缓酌樽中酒,容调膝上琴
童年转瞬即逝。
地瓜不再是农村越冬的主食,地瓜窖失去了意义,我对促织的兴趣被更多的事情取缔。
白洋河的水流越来越少,国营酒厂不再收购地瓜干,母亲得以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她的双手关节越来越粗,双腿膝盖越来越弯。
为方便静心学习,我搬到西屋夜夜苦读,睡梦中永远都是背不上的课文、答不出的考题,醒来依然焦头烂额、压力山大。窗外虫鸣依旧,却视作天外来客,心里竟有了 “少年不知秋,喜闻西风生。老大多感伤,畏此蟋蟀鸣”的沧桑之境。
哥姐们都到了婚嫁的年龄,我也去了另一个县的城里读书、工作。儿女们纷纷离开家,再也没见过母亲浆洗床单被褥,日夜操劳的父亲,仿佛一夜之间就白了头、驼了背。父亲去世不久,母亲也离开老家。曾经温暖有爱的老屋变得低矮、冷清、破败。我其实很想知道,老屋荒废的三十个秋冬,是否依旧有促织在曾经温暖的灶台前、炕洞里欢蹦?

母亲年届八十患上阿尔默茨海默症,她用天马行空的思维和不可理喻的行为将我折磨得欲哭无泪、生无可恋,而她自己却一脸无辜、一往情深。我努力克制自己的坏情绪,眼前晃动着她浆洗被褥、穿针引线时慈爱、安宁又满足的笑脸,晃动着她在月光下擦地瓜干时孤独、执着又倔强的身影,耳畔回荡着她“浆浆捶捶”的轻语,她擦地瓜干的急促声,回荡着促织清脆空灵的鸣唱……
四年后海棠花开繁花似锦的时候,母亲安静地离开了我们。我不用再含辛茹苦地照顾她,身体和心理皆解除重负,反而大病一场,精神感到无比荒芜:将我带到这世上的两个人都永远离开了我和这个世界,以至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有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我用童年治愈一生。
人生过半,生命之秋,才真正领悟元稹《处暑七月中》 “缓酌樽中酒,容调膝上琴”的从容与宽平。立秋之后,常倾心聆听窗外或路边草虫的吟唱,童年的回忆涌上心头。素手寻弦,弹一曲绵长悠远的《平沙落雁》,或空灵清雅的《鸥鹭忘机》,沧海桑田,春华秋实,潮起潮落,悲欢离合,都成过往。
琴声与虫鸣两相和,是为知音。
【编者按】蟋蟀又名促织,以聒噪歌唱冠名,庄家野地里的寻常物,在这篇文字里却是伴着作者成长的玩伴知音。这篇文字采用奏鸣曲结构,全文四个“乐章”,每个乐章皆用诗句做题目,从促织第一声鸣叫开始了独奏曲的弹奏,“瞿瞿嘘嘘”“浆浆捶捶”,秋天的况味开始出来了,孩子们欢乐的乐章也紧锣密鼓地奏响了。促织的奏鸣曲里,妈妈的身影贯穿始终,促织的叫声里,妈妈忙里忙外,浆洗被褥,田里劳作;促织的叫声里,孩子们的童年无比欢畅,闲来就找虫鸣,夜里在熟悉的乐章里安睡。乐章四个章节推进,渐近尾声,岁月在虫鸣中流淌而逝,母亲现在像个顽童般返老归真了,“我”也好久不闻虫鸣,今又听到虫鸣,恍然隔世般,一切都变得“从容宽平”了。这篇散文读着让人眼热,岁月深处的促织奏鸣曲疗愈人心。推荐阅读。编辑:梁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