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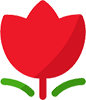 2
2

在我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旅途中,养过一只狗。后来再没养过狗,说来算是有点“曾经沧海”的念想。倒不是那狗长的比世上的狗都俊,而是它的死令我伤痛——它死在那个特殊年代所向披靡的“打狗运动”,一个大活人非但救不下一只狗,还得心不甘情不愿的亲手将其送死,否则有可能活得“狗都不如。”弃狗而自保,背后是人的自私,狗没出卖我,结果被我卖了。纵然是不得已,可我心里就是解不开这疙瘩。狗尚如此,人何以堪?于是,那只狗成了我惨痛记忆的一个具象。
上世纪60年代末,不满16岁的我被迫辍学,随同母亲和妹妹弟弟来到早年外祖父一家逃荒落脚的庄子(右派父亲单独在老家监督劳动)。开始,生产队不愿接收,因为争吃他们本不富裕的口粮,后来几经周折,终于落了户,接收原因其实非关狗屁政策,还是老乡亲感念外祖父一家的旧情。仅此一端,便让我深深体味到农民的朴实与仗义。
乡下10年,俺们娘几个艰难的苟活在极度困境中,同时也得到乡亲们许许多多恩惠与帮助,都是终生不能忘怀的。而自始至终给了我们极大眷顾与依赖的,是早年收留外祖父一家的姓任的“地主”。那个在革命教材里理应“青面獠牙”的“地主婆”却是善良温厚贤名远播的女菩萨,庄上老老少少无人不敬,外婆以及母亲当年就给她家做些零活,时常得些接济度日。母亲喊她“六婶子”,我叫“六姥”。六姥待我仁慈如母亲,我到六姥家渴了就喝饿了就吃,跟自己家一样。
那时正“学大寨”,庄上所有“黑五类”及“子弟”夜间都在地里守着机井放水,夏秋浇稻田,冬春灌小麦,人不够,再指派贫下中农子弟。极左年代,有个顺理成章无人违逆的定规:但凡脏活累活乃至无人敢上的险活,均由“阶级异己分子”打头阵,颇有点打仗推在前边挡枪子的味道,正像雷锋同志说的,“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当然,对待“准敌人”也照此办理。
我在乡下6年多,基本没在家睡过觉。刚开始年幼胆小,黑漆漆的夜里,孤身抛置荒郊野外,到处都是野坟,那种惊憟恐惧莫可名状,风吹草动,头皮一阵阵发紧,却又无计可施。赶巧,六姥家的母狗生下一窝小狗,还没满月,我如获至宝地抱了一只。那是一只卷毛的黄狗,不到半年,长得比一般狗都大,我就叫它大黄。
我对大黄的珍爱与依赖莫可替代,碰到啥好吃的,有我的必有它一口。白天我在窑厂干活,它就趴一边等我放工。到晚上,我用一根洞箫挑起铺盖,跟大黄一起到地里放水。夜里稍有动静,大黄便竖起耳朵,我不让叫它便停止,从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声音向我示警。若是有人或别的什么向我做出侵犯的举动,它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
阴湿的夜里,它敢追逐坟头上飘动的磷火,庄上人都说是条好狗,据说很多狗见了“鬼火”是不敢上前的。大黄不会看钟表,可是对时间的判断记忆比人还准,一到晚上那个钟点,它就到处找我,不安分地扯我,那意思该走了。一时找不见我,便飞跑到地里,地里不见,又飞跑回来,一找到我,那股兴奋别提了!
大黄对箫声也极敏感,我吹箫时,它就伏下不跑不动,有时我刚拿起箫,它马上伏下来望着我,简直是个知音。有时候,月光之下,我在地里吹起洞箫,不一会,远远地看见一条黑影由小变大箭矢般向我射来,那是大黄,我常常用箫声召唤它。
大黄有时像小孩一样,也会淘气犯错。有一回家里没人,它尽情地戏耍几只鸭子——把鸭子赶在一堆仿佛开会,哪个走开,它便跑过去咬着脖颈拎过来,如此拎来拎去,鸭子终于都伏下不跑了,到响午母亲从地里回来,6只鸭子奄奄一息,后来活了2只。大黄自知闯下大祸,一溜烟跑向庄外,到晚上都不见回来。一家人到处找,以为它从此不辞而别。过两天,母亲到几里外我小姨家,突然看见它,它一头钻进床底不出来。我姨家从前带它去过的,怎么也想不到它会跑到亲戚家躲祸,真叫人哭笑不得。
那天傍晚,母亲好哄歹哄带它回家,它一看见我,拼命摇尾巴又低着头乱躲,嘴里鸣鸣地仿佛认错,我差点没掉下泪来,心底下早原谅它了。只是那两只鸭子见了它嘎嘎乱叫起来就跑,像见了瘟神一般。
有回我带大黄经过一个庄子,一群狗上来围攻,大黄表现得极其勇敢,最后把一群狗咬得败阵而逃,回到家满身是伤趴着不动,我怕它会死,天天用盐水给它洗伤抹药,它痛得颤抖着身子呜呜低叫,令我想起关云长刮骨疗毒,紧要关头未必狗就不如人。
先是风传城里掀起“打狗运动”,说狗是传染病源。后来有城里的亲戚把狗送到乡下躲避,总以为乡下地广人稀,不会也打狗吧。再后来生产队开会果然布置打狗。那年月打狗也是政治任务,谁敢抗拒?自古以来,犬守夜,鸡嘶晨,蚕吐丝,蜂酿蜜,天然四宝,都是与人类声气相通和谐共处的动物,尤其狗,早已深通人性,与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奈何运动一来,连狗也遭灭顶之灾。而谁家又忍心下手打死养得热热乎乎浑如家人一口的狗呢?于是母亲拿一堆好吃的让大黄吃,一边像叮嘱孩子一样叮嘱它:跑的远远的,别回来!大黄完全能听懂的,一步一回头跑走了。白天没见回来,晚上却跑到地里找我,可见它对这个家是多么依赖。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个政策下来都打狗,又能逃到哪去?后来“打狗队”就到家威逼:“贫下中农的狗都得打,何况你们啊?!”
这么一来,狗和人都被逼到了绝境。那一天,庄上一下来了十几个杀狗的,当然是上边安排的,仿佛鬼子进村扫荡一般,全庄的狗齐声狂吠作垂死的抗议,惨叫声此起彼伏,一只只狗被铁钳夹住脖子嘴巴穿上铁丝血淋林地拖走,有的现场用棍打闷或吊在树上勒死。大黄是被一个浑身狗腥气秽不可闻的麻脸逮走的,可知他杀了无数的狗。我永远忘不了嘴上滴着血的大黄回头看我那哀戚绝望的眼神——此后便常常出现在梦里。
从那,我再没养过狗。
【编者按】一篇《怀念狗》说的是狗,倒不如说那么一些经历过的日子。过去的农村,许多家庭都会养狗,一是可以看门护院,二是可以吃它的肉。狗是懂得事理的,许多时候,人还不如狗的心肠好。现在更是不同了,抱着一只狗叫宝宝,而对于年老的父母却是不闻不问,诸如此类的人,也算是一个动物。散文作家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中也讲到过一只狗。狗作为动物的一种,是有许多事情可写的。倾情推荐阅读。编辑:李金松


